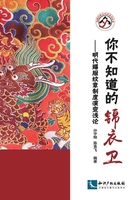
第一章 明代官僚体系和赐服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在元末风起云涌的乱世中,他就参考元代的旧制,在自己的部队中设立官职。
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陆续有来自各地的武装势力投靠或者归降到他的麾下。这些来自群雄的部队,往往是整建制的来投,初期都保留了自己的称谓,多称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等。一直到甲辰年(公元1364年)他称王以后,对投靠自己的队伍进行了一次整编,订立了“部伍法”,统一了部队番号以及职官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中年龙袍画像
“初,上招徕降附,凡将校至者皆仍其旧官,而名称不同。至是下令曰:为国当先正名。今诸将有称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者,名不称实,甚无谓。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令既下,部伍严明,名实相符,众皆悦服,以为良法。”(《太祖实录》)
“甲辰整编”的实施,奠定了明代的武官制度,即“卫所制度”。而元代所实行的“军户世袭制度”,也被明代所继承,成为卫所制度的一大特征,这从存世的各种武职“选簿”内黄外黄(古时职官的档案册)的记录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实例证据。因此可以说:武官的世袭制度早在大明建国以前就开始实行了。明代的武官,以卫所系统的武官为主,兼有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种宣慰司、宣抚司或者羁縻卫所中的土官。卫所系统的武官,分为世官和流官两种,其中世官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千户、副千户、所镇抚、百户、试百户,这九等武官皆可世袭。流官八等,系五军都督府和都司、留守司中的高阶武官,包括: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留守、副留守,这八等流官皆不许世袭:
“国家设都卫节制方面,所系甚重。当于各卫指挥中,遴择智谋出众以任都指挥之职,或二三年,五六年,从朝廷升调,不许世袭。”(《太祖实录》)
一旦被授予武职,就有相应的勋、禄和散阶,比如正二品都指挥使:勋号上护军,禄米六十一石,散官初授骠骑将军,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与之相应的,文官系统也有相应的勋、禄和散官。
表1 明代官职品禄表

最初朱元璋在建立政权的时候,是采取元代的旧制,设立枢密院。甲辰整编的时候,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在定鼎天下之后,最先朱元璋在帝国的中央采用的是唐宋沿用的三省六部九卿的制度,后因胡惟庸案而撤销了三省,收回了相权。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下诏:“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实时劾奏,处以重刑。”胡惟庸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
在取消相权之后,朱元璋创立了一个六部平行的机制,即各部互不隶属,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旋即又设置“四辅官”,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通纪》载:
“九月丙午,置四辅官,以耆儒王本、杜佑、袭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位列都督之次。敕以协赞政事,均调四时。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时若,验其称职与否。”
不久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以大学士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职务。《昭代典则》说: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使侍左右备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召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
内阁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僚机构,仅仅是皇帝召集一些文官、甚至是低阶文官来襄赞政事。久而久之,阁臣们不断升迁,由大学士而尚书、侍郎,进而位列三公,权力也越来越大。嘉靖朝阁臣们甚至位列六部尚书之上,俨然如唐代的门下省。由于唐代门下省的官员互称阁老,因此内阁大学士们也被尊称为阁老。内阁甚至在某些时期僭越了皇权,名臣张居正即是此列,他也开创了“文官赐蟒”的先河。

张居正着蟒袍像
“三公”和“三孤”,即正一品官太师、太傅、太保和从一品官少师、少傅、少保,本来是负责辅佐皇帝的重臣,到了明代,这一品文官职就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了,而成为对勋官文官的加官或者赠官。据载,翊国公郭勋和成国公朱希忠曾经遍历“三公”,一时为人称道。文官能够不依靠军功加官到太师,可谓是位极人臣了。有明一代,即使权势熏天如严嵩、徐阶,最后获得的加官也仅仅是少师。张居正却是在活着的时候一加少保、太子太保,再加兼太子太傅,三加少傅,四加太子太师,五加少师,六加太傅,七加太师,因此当年明月送给他一个雅号“首席活太师”(当然活着的时候获赠太师衔的还有好几位,比如李善长、张辅、朱永、朱希忠、魏良卿,其实还有朱寿,只不过他是自己给自己加的,也算上吧)。
“六部”是国家事务的具体管理机构,分管官员人事、财政、国防、礼仪、民政等职,百度上对其描述颇详,摘录如下:
“明朝中枢设六部。吏部有尚书(正二品)一人,左右侍郎(正三品)各一人,下设四个清吏司(文选、验封、稽勋、考功),每司各有郎中(正五品)一人,员外郎(从五品)一人,主事(正六品)一人等官。吏部职权特重,为六部之首。户部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十三清吏司(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户部另有一些直辖机构,如宝钞提举司、广盈库、军储仓等。礼部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四个清吏司(仪制、祀祭、主客、精膳),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另辖铸印局等。兵部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四个清吏司(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另辖会文馆等机构。刑部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十三清吏司(分司同户部)。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工部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四个清吏司(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另辖宝源局、军器局等机构。
旧都南京也设六部,称南六部,另有一套职官,但又不全置,其职权远不如北京六部。一般是安置地位崇高之退闲大臣之所。”
在六部以外还设有六科给事中,相对于六部,职责是监督六部的工作。给事中品级很低却直接向皇帝负责。这个部门也是明代的创举。

徐显卿宦迹图之皇极侍班
“五寺”即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其中大理寺类似全国最高法院,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后来锦衣卫的出现一定程度侵占了三法司的权力。太常寺管理祭祀事宜,光禄寺管理宴会,太仆寺养马,鸿胪寺管理外交事宜。
都察院的前身是御史台,其负责人为左都御史,下辖十三道监察御史共一百一十人,职责是纠察百官。监察御史,又称巡按,“代天巡守”说的就是这些人,品级虽然不高,但是权力极大。
元朝曾设有“四方献言详定司”来采纳来自各方的意见建议,修订政策。明朝在洪武十年(1377年)设置了“通政使司”掌握内外章奏、封驳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参与仪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通政使司是明代创设的,其职能似乎有类于南北朝的通事舍人、唐代的知匦使、宋代的閤门使及通进银台司等机构的合并,在理论上是君主和臣下之间的一个联系机关,任何官署上奏事件都必须经由其手,所以居七卿之下的最高位次,有资格参与“廷推”。据《梦余录》记载,通政司门下有一红牌,书云“奏事使”,持此牌可以直入内府,守卫官不得阻拦,这给通政使奏事提供了方便,使下情能及时上达。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其封奏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天顺以后,其作用虽稍减弱,但也为权奸所警戒;其主官是通政使正三品。通政使和大理卿、左都御史以及六部尚书的组合就是明朝文官的“第一天团”——“九卿”。
翰林院是文官的“孵化基地”,凡科举高中的状元、探花、进士等必先授翰林,之后才逐渐升迁。
詹事府则是辅佐东宫的官员。宗人府管理老朱家一大堆的子孙后代的事宜。此外,“京官”还有国子监,是最高公立学府;太医院负责看病;钦天监负责观测天文、颁布历法、替皇帝算命等工作。

徐显卿宦迹图之司礼授书(教太监读书)
地方官员则有都指挥使司、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即所谓“三司”,来管理军政以及司法工作;另有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监督。各府、州、县官员由中央统一派任。
除文武诸司官员以外,明朝历史上还有一类官员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这些人就是宦官。宦官,或称内官、内使、中官、中使。建国之初,朱元璋对太监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好的,他认为“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此外他还定下规矩:“内侍毋许识字”。他还铸造过一个铁牌曰:“中使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同时又下诏给政府各部门:“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然而到了永乐年间,由于皇帝屡屡派宦官出使、监军、巡边,使得太祖的祖训就此作废了。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的事迹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宦官的组织机构,常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
“《皇明祖训》所载,设立内府衙门,职掌品级,立法垂后,亦尽善尽美。惟是间有《祖训》所未及载,或载而未详者,谨谱次梗概于左。按内府十二监:曰司礼,曰御用,曰内官,曰御马,曰司设,曰尚宝,曰神宫,曰尚膳,曰尚衣,曰印绶,曰直殿,曰都知。又四司:曰惜薪,曰宝钞,曰钟鼓,曰混堂。又八局:曰兵仗,曰巾帽,曰针工,曰内织染,曰酒醋面,曰司苑,曰浣衣,曰银作,以上总谓之曰‘二十四衙门’也。此外,有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等处。”(《酌中志》)
除此二十四衙门以外,还有各王府供奉的宦官,孝陵神宫监、天寿山守备太监、凤阳守备太监、湖广承天府守备太监等,其中以“司礼监”的地位最为显赫。司礼监最高阶者称“掌印太监”,其次是“秉笔太监”和“随堂太监”。这些太监每日的工作就是帮助皇帝批奏折。在明朝中后期,这些中官凌驾于外臣之上替皇帝行使皇权。司礼监还执掌着东厂的权柄,因此能够进入司礼监就等于进入了帝国的政治核心。有明一代著名的“立皇帝”“九千岁”们,无一不是出自此监。只要进入了司礼监,就获赐了高阶的赐服,全员穿着曳撒,起初是斗牛,次升坐蟒。二十四监中也有“神宫监”“直殿监”和“都知监”这类负责祭祀洒扫清道的“清水衙门”,一旦进入这些部门,就会被认为政治前途一片黑暗——“下下衙门也”。
以上所述,加上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官,即组成了明朝的官僚体系。
明代建国,朱元璋就建立了明代的冠服体系。洪武元年,皇帝就曾经下诏:“复衣冠如唐制。”但是由于时间太久远,所以当大臣们向皇帝奏请恢复古代的“五冕”制度的时候,遭到了皇帝的拒绝。洪武三年,皇帝又说今“服色所尚于赤为宜”,到了洪武二十四年,皇帝又召集礼部和太常寺的官员大讨论,更定冠服制度。此后历代皇帝又陆续提出了对官民人等服色的一些限制,比如“大红紵丝、纱罗”这种颜色质地,是极高的荣誉,一般的官员都不允许服用:
“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尚宝司、光禄寺、鸿胪寺五品堂上官、经筵讲官方许穿用,其余衙门虽五品官及五品以下官,经筵不系讲官者俱穿青绿锦绣,遇有吉礼,止许穿红布绒褐。”(《明会典》)
又如织金妆花、五彩闪色等工艺,只允许皇家使用,民间不得织造和使用:
“在京在外官民人等不许滥服五彩妆花、织造违禁颜色及将蟒龙造为女衣,或加饰妆彩,图利货卖。”
“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缘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服饰、器用等物并追人官。”(《明史·舆服志》)
而这些禁用的面料,却常常出现在皇帝赠赐给大臣、内官、皇亲、边臣和少数民族领袖的物品中。
对于服饰纹样的限制,洪武三年规定:
“不得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
“凡民间织造违禁龙凤纹芝丝、纱罗货卖者,杖一百,段匹入官。机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
“官吏、军民人等,但有僭用玄、黄、紫三色及蟒龙、飞鱼、斗牛,器皿僭用朱、红、黄颜色及亲王法物者,俱比照僭用龙凤文律拟断,服饰器物追收入官。”(《明太祖实录》)

飞鱼锦缎(东京国立博物馆)
天顺二年(1458年)有令:“官民人等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而这些图样的禁止,是为了维护皇家的权威,这些纹样只允许出自皇家的赏赐恩典。比如皇帝的家奴——中官,只要中官能够进入司礼监,就可以穿着斗牛曳撒;资深的太监们几乎都是穿着高贵的坐蟒服,这种荣宠让外臣们望尘莫及:
“按《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万历野获编》)
在《明史·舆服志》中,详细规定了皇帝、后妃、太子、亲王、郡王、世子、百官、退休官员、僧道、庶人的服装制度,其中还包括了附属于大明王朝的外国君臣的服色:
“外国君臣冠服:洪武二年,高丽入朝,请祭服制度,命制给之。二十七年,定蕃国朝贡仪,国王来朝,如赏赐朝服者,服之以朝。三十一年,赐琉球国王并其臣下冠服。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带,视二品秩。宣德三年,朝鲜国王李濩言:‘洪武中,蒙赐国王冕服九章,陪臣冠服比朝廷递降二等,故陪臣一等比朝臣第三等,得五梁冠服。永乐初,先臣芳远遣世子禔入朝,蒙赐五梁冠服。臣窃惟世子冠服,何止同陪臣一等,乞为定制。’乃命制六梁冠赐之。嘉靖六年,令外国朝贡入,不许擅用违制衣服。如违,卖者、买者同罪。”

明朝中后期重臣李成梁画像(身着四爪蟒袍)


李成梁画像 局部
这种对附属国君臣的赐服,是明代赐服制度的一个典型例子。皇帝通过赐予附属国相当于中央王朝郡王甚至亲王级别的冠服,来表示对其地位的承认。这种制度也不是明代的独创,历代中原王朝都有赐予前来朝贡的外国官员和君主冠服的旧例。这是基于自古以来的“朝贡体系”和“中央王朝”的思想。明代建国以后将这种非常规性的赏赐制度化了。这一类赐服的范围包括了朝鲜、琉球、越南等国家的君主和使臣,以及明帝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教领袖,比如西藏的活佛、法王、大喇嘛等,虽然后者在后来的历史中常常因为帮助皇帝生儿子而获赐更多的高阶服装和金银珠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这一赏赐又泽及了苏禄(今菲律宾)、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王国)和文莱等国。前几年文莱苏丹即位的仪式上,最靠近宝座的两个礼仪官员,其中的一个穿着明代式样的官服,据说即是来自明代的赏赐。后来的“壬辰倭乱”以后,皇帝又给日本太阁丰臣秀吉赐了诏书、皮弁服和麒麟、飞鱼等,相当于郡王等级的高阶纹样的服装。

万历赐给丰臣秀吉麒麟袍柿蒂窠 局部(日本妙法院藏)
除了这些外国君臣,一些内附于明帝国的边疆守将或者效忠于皇帝的蒙古诸部领袖和将领也经常向朝廷请赐高级服色纹样的官服。《宪宗实录》中记载,成化元年:
“泰甯等卫右都督列玉、突兀南帖木儿,乞地市牛只农具,许之,求蟒衣不得。”
“迤西癿加思兰与其妻奏求蟒龙等服,诏不允,以红绢及毡衫与之。”明人笔记中又有:
“正德中,赐播州宣慰司杨斌麒麟衣一袭,升四川按察使。后以宣慰致仕,复赐麒麟衣一袭,最后赐蟒衣、玉带。以贡物厚故也。赐永顺宣慰使致仕彭世麒大红蟒衣三袭,升都指挥使;其子宣慰明辅大红飞鱼服三袭,给正三品散官诰命。以进大木故也。嘉靖末,复以进大木赐致仕宣慰彭明辅蟒衣,进湖广都指挥使,致仕;子宣慰翼南飞鱼衣一袭,进云南右布政使。正德赐日本使臣宋素卿大红飞鱼服一袭。中人瑾受其黄金故也。素卿,闽人,至嘉靖中,始以争贡事论死。”(《万历野获编》)
在明人的笔记中,这些边疆的土官因为进贡木材之类的事情获赐高级的赐服。而文中提到的宋素卿,却是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赐服。正统年间出于怀柔目的的对于瓦剌部的殊赏,则引起了当时的社会对“北人之赏”的关注:
“赐北人之厚无过于正统时,卫拉特布哈王太师额森者,盖其时敌势方盛故也,按四年赐托克托布哈王汗者织金四爪蟒龙膝襴八宝衣一、织金胸背麒麟青红彩段六、五色段八、绢二十五、金嵌宝石绒毡帽一顶、金鈒大鹏厌缨十件、全伽蓝香间珊瑚帽珠一串、宝金彩绣紵丝衣六、金绣缠身蟒龙直领一、青暗花井口对襟曳撒一、织金胸背麒麟并四宝四季花褡护比甲各一、织金虎并圈金宝相花云肩通袖膝襴各一、金相犀甲麒麟系腰一、红甸皮描金花包二、鋄银折铁刀并鞘一、铜线虎尾三、尖云头套靴一双、秋水面乌木裹琵琶一、花梨木哈必苏一、鞭鼓喇吧号笛各一、黄身勇字鱼肚旗一、鱼尾号带飞虎招旗二,妃及丞相知院大夫以下各有差赐,淮王额森与汗同。自是岁岁有加十四年又赐汗织金蟒龙文绮彩绢一百八十四疋、金银各五锭塔纳珠一千六百颗、金银镶木碗各二、织金九龙蟒龙浑金文绮三十八疋、绣金衣五件、靴袜乐器账房药材等物。可汗二妃织金文绮彩绢三十二疋、各锦袍一袭、织金衣三件、靴袜针线脂粉丝绒具全。赐额森亦如之。未几而有土木之变,尚赐可汗及额森各金百两银二百两、大珠十塔纳珠百颗、织衣九龙紵丝五疋、织金蟒龙紵丝五疋、织金胸背紵丝十疋、浑织金花紵丝五疋、素花紵丝二十疋、并琵琶筝胡琴器皿等物。”(《皇明异典述》)
“北虏之赏,莫盛于正统时,其四年及十四年者,弇州《异典》,已尽记之矣。惟六年之赏更异,今录之:赐可汗五色彩段,并紵丝蟒龙直领、褡护,曳撒、比甲、贴里一套,红粉皮圈金云肩膝襴裙通衲衣一,皂麂皮蓝条钢线靴一双,朱红兽面五山屏风坐床一,锦褥九,各样花枕九,夷字《孝经》一本,锁金凉伞一,绢雨伞一,箜篌、火拨思、三弦各一幅,并赐其妃胭脂绒绵丝线等物。至八年,又赐可汗紵丝盛金四爪蟒龙单缠身膝襴暗花八宝骨朵云一疋,织金胸背麒麟白泽狮子虎豹青红绿共四疋,八宝青朵云细花五色段二十六疋,素段五十六疋,彩段八十七疋,印花绢十疋;可汗妃二人白泽虎豹朵云细花等段十六疋,采段十六疋,花减金铁盔一顶,戗金皮甲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拨思、胡琴等乐器,及钻砂焰硝等物;又赐丞相把把只织金麒麟虎豹海马八宝骨朵云紵丝四疋,彩绢四疋,素绢九疋;其余平章伯颜贴木儿小的失王,丞相也里不花、王子也先孟哥、同知把答木儿、佥院南刺儿、尚书八里等,皆赏彩段绸绢有差。上又赐御书谕太师淮王中书右丞相也先,赐织金四爪蟒龙紵丝一、织金麒麟白泽狮子虎豹紵丝四,并彩绢表里;又赐也先母妃五人、妃四人、诸织金缯彩。”(《万历野获编》瓦剌厚赏条)

镇朔将军唐通像轴(故宫博物院藏)
(唐通于明亡前夕居宣化总兵、密云总兵等要职。手握兵权,举足轻重。崇祯皇帝曾召见唐通并赐莽玉,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但唐通终负所托,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身份变换不定。《清史列传》将其列入《贰臣传》)
文官们也许是出于嫉妒,于是请求皇帝下令整顿赐服的秩序,弘治元年正月:
“甲子,礼部以左副御史镛赐蟒衣。《尔雅》云:蟒者,大蛇,非龙也。蟒无角无足,龙则角足具焉,今织蟒俱为龙。遂禁赐并纺织者。”(《万历野获编》)
“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明史·舆服志》)
关于大臣们的赐服,在国初,著名者有常遇春。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张由常遇春后人提供的常遇春画像。在这张画像中,常遇春头戴唐巾,耳戴金环,身穿盘领长袍。令人惊奇的是,开平王常遇春身穿的红色圆领袍上的纹样,是一条缠身过肩的五爪金龙!这件衣服据说是来自皇帝朱元璋的特典,是皇帝在常遇春死后脱下自己的龙袍赠送给他的,之后还下令追绘了常遇春身穿这件龙袍的影神像以示荣宠。皇帝赐予臣下龙袍这件事情在明初可谓是特典。

常遇春画像(着五爪金龙圆领袍)
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就是滥典了,皇帝不得已将“五爪龙文”的赐服称之为“蟒龙”。《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就说过:“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换句话说,同样一件衣服,如果穿在皇帝的身上就叫作“龙袍”,而如果颁赐给臣下,就被称为“蟒龙袍”了。考内阁大学士赐蟒衣,始于弘治十六年大学士李东阳、刘健、谢迁,大抵是为了表彰他们领衔编修《大明会典》。万历年间的权臣张居正,则是开了“文臣赐坐蟒”的先河。所谓“大红色坐蟒”,乃是有明一代最高贵的赐服。这种殊荣,却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
“永顺伯薛勋及广甯伯刘佶俱乞赐蟒衣,上曰:蟒衣之赐系朝廷特恩,今后有如此者,必罪不恕。”(《明孝宗实录》)
“定国公徐延德宿卫,南郊请以蟒衣扈从,上曰赐蟒系出特恩,何輙自请,不许。”(《明世宗实录》)
“总督京营戎政、忻城伯赵世新奏,乞照例给盔甲蟒衣以便护卫,许之。礼部言蟒衣服色《会典》不载,陈乞已非,且凡有奏讨,无不下部议者,今若此,部覆可废乎?谓祖制,何不报?”(《明神宗实录》)《明史·食货志》载:
“正德元年(1506年),尚衣监言:‘内库所贮诸色紵丝、纱罗、织金、闪色蟒衣、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
在正德皇帝上任的第一年,内府库的高阶纹样的布料已经用完了,而这位皇帝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他行为放荡不羁,视封建秩序如儿戏,对于高阶纹样服饰的赏赐,他向来是毫不吝啬。除了前引史料中赏赐西南土官的例子以外,“应州大捷”后正德十三年车驾还宫的赏赐事件到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明史·舆服志》)
皇帝把内府库的库存全部拿出来,让京官们连夜赶制成曳撒服,第二天到城门去迎接皇帝的车驾。平日里文官们羡慕的高级纹样,简直是雨露均沾地发放到每一个京官的手里。更不用说皇帝还朝以后论功行赏,升赏叙荫共计五万六千四百多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冒功,而由于兵部和中官朋比为奸,这些冒功者到了嘉靖时期才受到处罚。在这期间,中官们大肆在锦衣卫和其他卫所部队里安插自己的亲属,并且恣意给他们封爵:
“平凉伯马山,提督东厂太监永成侄也。镇平伯陆永,监枪太监訚侄也。皆冒永等恩泽封,后具革。马山虽贵,衣蟒围玉为永成汲水浇花调马于庭,他亦往往类是。”(《皇明异典述》)
这位伯爵马山,没有任何的军功,可能连朝阳区都没有出过,只是因为他是厂公马永成的侄子,就被封为伯爵,穿着蟒袍围着玉带在院里浇花喂马,直到嘉靖年间被革除了爵位。

明武宗
不过武宗朝最后,蟒袍似乎已经不值钱了:
“壬戌自刘瑾专政以来,名器僭滥。以蟒鱼服色为黩货之资,武将阉臣下至厮餋,陈乞纷然,时有五十两一件蟒之谣云。”(《武宗实录》)。
嘉靖年间,世宗皇帝对前任皇帝大量恩封赏赐这件事情意见特别大。皇帝革除了正德年间冒领军功的宦官子弟,裁汰了锦衣诸卫和内监局的冗员十四万八千七百人,把正德年间恩赏恩封的权贵子弟一多半都革除了,并且遣散了豹房的番僧道士和乐师,同时下诏重申了对禁用纹样的使用限制:
“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明史·舆服志》)
嘉靖十六年,
“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其大红紵丝纱罗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五品堂上官、经筵讲官许服。五品官及经筵不为讲官者,俱服青绿锦绣。遇吉礼,止衣红布绒褐。品官花样,并依品级。锦衣卫指挥,‘侍卫者仍得衣麒麟,其带俸非侍卫,及千百户虽侍卫,不许僭用。'”(《明史·舆服志》)
兵部尚书张瓒也是属于没眼力见儿的,因此受到了皇帝的批评。而锦衣卫官员,在御前侍卫且有官职的,才允许服麒麟。带俸的挂名锦衣卫,或者御前侍卫而级别不够的,也不允许服麒麟服。需要皇帝下令规范赐服,足以说明在当时的社会蟒衣飞鱼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
而到了万历年间,似乎对于锦衣卫官员的服饰又重新开禁了:登大堂者,拜命日即绣春刀鸾带大红蟒衣飞鱼服,以便扈大驾行大祀诸礼。其常朝亦衣吉服,侍立于御座之西,以备宣唤,其亲近非他武臣得比。以故右列艳之,名为武翰林。”(《万历野获编》)
“至尊初登极,行郊祀大礼,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俱赐大红织金紵袍。若恭谒诸陵及行大阅,则内阁辅臣俱赐蟒衣,或超等赐服,至鸾带金银瓢绣袋等物,以壮扈从。其次即日讲官,以至文武勋戚、部府大臣,俱沾绣带采带之赐。皆主上肇行大礼,特恩殊典一次耳。惟阁臣未及受赐者,则于嗣举补给,他官不尔也。又锦衣卫官

出警入跸图 局部
看起来,神宗也毫不吝惜对文武大臣的赏赐。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出警入跸图》清晰地展现了皇帝前往昌平天寿山谒陵的仪仗,其中内官、锦衣卫、文武官员甚至乐师校尉等皆服色锦绣灿烂,可以清晰地看见其中的织金蟒龙、飞鱼、斗牛的纹样。

出警入跸图 局部
而对于另一类人的封赏,嘉靖皇帝就更毫不吝啬了:
“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自是以为常。内阁赐蟒衣,自弘治中刘健、李东阳始。麒麟本公、侯服,而内阁服之,则嘉靖中严嵩、徐阶皆受赐也。仙鹤,文臣一品服也,嘉靖中成国公朱希忠、都督陆炳服之,皆以玄坛供事。而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青词,亦赐仙鹤。寻谕供事坛中乃用,于是尚书皆不敢衣鹤。后敕南京织闪黄补麒麟、仙鹤,赐严嵩,闪黄乃上用服色也;又赐徐阶教子升天蟒。万历中,赐张居正坐蟒;武清侯李伟以太后父,亦受赐。”(《明史·舆服志》)
孔门圣裔的衍圣公,历代封为伯爵,景泰年间开始赐织金麒麟袍并玉带。而内阁大学士身为文官,服用武官或者公侯的麒麟服色,也属于破例。嘉靖皇帝经常给臣下赐仙鹤纹样,这就跟皇帝信仰的道教有关系了。然而仙鹤纹样本来就在国家品官纹样体系中,本来应该是一品二品文官的服色,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严讷、李春芳等,以五品而获赐仙鹤服色,让皇帝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然而已经说出去的话不能反悔,皇帝更是金口玉言,因此只好再下一道圣旨,说今后只能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才可以衣鹤,其余都不可以衣鹤。结果真正的二品官员们不敢穿仙鹤纹饰,只好穿锦鸡纹样的服装,而那三位五品大学士,则大摇大摆地穿着仙鹤服色四下招摇。王世贞是个老学究,为人很严谨,想来是不会故意抹黑嘉靖皇帝。有关内容,在王世贞的笔记《皇明异典述》中,更为详细:
“赐衣文武互异 嘉靖中,内阁严、徐、李皆赐服麒麟。麒麟,公侯服也。而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左都督陆炳等,以玄坛供事,特赐服仙鹤。仙鹤,文臣一品服也。成化以后,文臣赐麟不为异,而公、侯、伯武臣赐鹤则异矣。六公出入朝行,殆不可复辨。
五品鹤袍 嘉靖中,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玄词,特赐仙鹤袍。既而,上悔之,下谕谓‘玄坛供事可用鹤,余则不可’。意盖为三臣也。而尚书皆自疑,不敢衣鹤,亟市锦鸡为饰,而三学士之衣鹤自若也。”
嘉靖年间著名的道士邵元节,在嘉靖十三年就获赐了蟒衣,后来官至礼部尚书,死后赠少师、赠谥号文康荣靖,可谓是位极人臣了。而他推荐给皇帝的另一个道士则更加倍受荣恩。
“陶仲文于真人之外,加至少师兼少傅少保并拜三孤,带礼部尚书封恭诚伯,则文武极品矣。”(《万历野获编》)

王琼事迹图册 局部(着织金仙鹤补)
陶仲文道士一开始只是黄梅县吏,后来做了辽东库大使,任满之后就开始了“北漂”生活,借住在邵元节府上。后来邵元节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把他推荐给了皇帝,结果皇帝对陶道士是一见倾心,二十多年里找各种借口封赏他,抓了个间谍也归功于他,求雨成功也封赏他,等等。
陶仲文到底有什么本事呢?首先可能是算卦比较灵:
“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史》)
其次,据王世贞的说法,他帮助皇帝生儿子:
“仲文立朝几二十年而不废,唯其呈内宫子嗣延法为最,传今上之降复出此,信然。”(《古今杂抄辑录》)
储君乃国本,而皇帝天天操劳过度,往往性生活质量不高。陶真人的法术,最主要还是能让皇帝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多生龙子龙女。嘉靖五十岁时,已有五子八女,所谓“皇子叠生”,所以皇帝对他的荣宠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嘉靖前后,赐真人陶仲文银十余万两、大红、金彩、绣织、蟒龙、斗牛、云鹤、麒麟、飞鱼、孔雀、缎罗纱绢无虑数百袭,狮蛮玉带、白玉带五围,金带一围,玉印二,金嵌宝冠、浑金冠、累丝冠、如意七宝簪、金嵌宝石、金银水盂、金盘、银盘各十余副。”(《皇明异典述》)
从这些记载中看来,前几年下旨要禁用蟒衣、斗牛、飞鱼的那个嘉靖皇帝全然不见了呢。顺便提一句,嘉靖皇帝还创造过一些赐服,比如赐给大臣燕居时穿着的忠静冠服和保和冠服,另外他还做了几顶“香叶冠”送给他的“同修”:严嵩、夏言等人。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局部
中官们由于靠近皇帝本人,因此普遍穿着高级的纹样,并形成制度。按《大政记》记载:
“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万历野获编》)
原则上中官的服装很简单,都是些青色绿色的直身或是窄袖圆领袍,而到皇帝身边值班的时候,就不能穿得这么寒酸了。
于是在靠近皇帝的职位上,基本的服色就是曳撒、大红色、斗牛纹样,稍稍高级一点,就赐蟒和玉带。这种在外官看来是隆恩的特典,在内官体系中只是制度化的“升授”而已。到明末,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对这种殊荣尚不满足,还“发明”了一系列的花式服装,比如九梁冠、三膝襴曳撒等,如是种种,已经出了赐服的本分了,所以被称之为“服妖”。这种“服妖”的行为,也被视为不祥之兆——“断送了卿卿性命”,甚至预示了大明帝国的衰落。
明朝的官僚体系对前代是有继承的,但是也不无创新,赐服制度是自古以来的服章礼仪制度的集中体现,虽然偶有崩坏,但是大致上还是可以看出其所代表的森严的封建等级秩序,其主要作用还是维护皇权和怀摄文武大臣,在有明一代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详细讨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