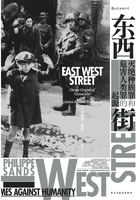
7
1923年,莱昂正在学习电气和技术科目,同时在姐夫马克斯的酒品店里帮忙,希望沿着父亲的轨迹接受同样的教育。我在他的相册中找到一些照片,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很像是老师的人。他仪表堂堂,留着髭须,站在花园中,面前的小木桌上摆满了蒸馏用的器材:酒精灯、烧瓶和试管。老师使用的原料可能是含有乙醇的谷物发酵液体。这种液体被蒸馏提纯后产生一种馏出物,即通过分离过程得到的酒精。
维也纳的现实生活与这个提纯的行为正好相反。在经济困难的时期,随着通货膨胀的失控和紧张局势的加剧,大量新难民从东边涌入。各种条件催化了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加上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兴起,各政治集团无法共同组建出能够正常运转的政府。于1918年在奥地利成立的地方党派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与它的德国分部合并了,其领导人是一个奥地利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1923年夏天,在出席姐姐劳拉和贝尔纳德·罗森布卢姆婚礼的两周后,莱昂为取得护照回到了利沃夫。尽管已经在维也纳生活了10年,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具有奥地利国籍。1919年6月,与《凡尔赛和约》同日签署的不起眼的《波兰少数民族条约》使莱昂成为波兰公民。20
该条约是为了强制其履行保护少数民族的义务而强加给波兰的。作为现代人权公约的早期雏形,该条约第4条的法律效力保证了1919年签署条约之前出生在利沃夫的任何人都将被视作波兰公民。无须填写任何表格,无须提交申请。“依据事实本身,无须办理任何手续”,该条约一经宣布,莱昂及生活在利沃夫和若乌凯夫等地的数十万居民就成了波兰公民。这件法律界奇事既是惊喜也是麻烦,后来还挽救了他和我母亲的生命。我本人能够活在这世上可以说是多亏了这个《波兰少数民族条约》的第4条。

莱昂的波兰护照相片,1923年
莱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离开奥地利伦贝格,随后这里陷入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当他回来领取护照时,这里已经变成了蓬勃发展的波兰大都会,充满了有轨电车刺耳的声音和“糕点房、水果摊、殖民地商店,以及埃德蒙·里德尔铺子和茱莉曼尼铺子散发的茶与咖啡的香气”21。波兰对苏俄和立陶宛的战争结束后,这座城市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1923年6月23日,利沃夫警察局签发了莱昂的新波兰护照。护照上写明这是一个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年轻人,但照片中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的衣着整洁利落:一件黑色外套、一件白色衬衫和一条引人注目的现代风格粗横条纹领带。虽然他当时已经19岁了,但是他的职业一栏仍标为écolier,即学生。
那个夏天剩下的时间他都是在利沃夫度过的,和亲人、朋友,包括他的母亲一起住在舍普季茨基街上。他会去若夫克瓦拜访莱布斯舅舅和那边的大家族,他们住在毕苏斯基大街上的一栋木房子里,就在犹太会堂北边不远的地方(几十年后,街道变成了泥巴路,房子也早已不在了)。莱昂可能喜欢去镇周围的小山丘散步,穿过东面边缘茂密的橡树和桦树林,也就是被叫作borek的地方。这一片是若乌凯夫的孩子们经常玩耍的地方,低矮丘陵中间的一片宽阔平原,紧邻通往利沃夫的主路。
8月,莱昂去了一趟位于布拉杰若夫斯卡街14号二楼的奥地利领事馆,就在大学附近。奥地利当局在这些租用的最后的堡垒里,为他加盖了单次往返奥地利的签证印戳。离法律系不远的捷克斯洛伐克领事馆为他提供了过境签证。在城市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与莱昂擦肩而过的很可能就有两名最终将在纽伦堡审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年轻人,他们那时才刚踏上职业道路:赫希·劳特派特于1919年离开这里前往维也纳求学,当时可能正返回探亲,同时在为了当选利沃夫大学国际法主席而努力;拉斐尔·莱姆金当时是利沃夫大学法学系的学生,住得离马尔卡很近,就在圣乔治主教座堂的脚下。这段时期塑造了他们,在利沃夫和加利西亚一系列事件的触动下,有关法律在打击大规模暴行中之作用的各种观念正在他们的脑中形成。
8月底,莱昂离开了利沃夫。他乘坐火车前往克拉科夫,这是一趟长达10个小时的行程,然后继续乘坐火车前往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南部边界的布热茨拉夫。1923年8月25日上午,列车驶入西北车站。莱昂从那里步行回到不远处的克洛斯特新堡大街上的古斯塔家。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利沃夫和若乌凯夫,据我所知,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家族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