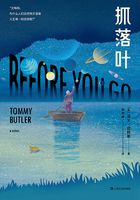
第4章 艾略特(1982)
我爱睡觉。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但是我没法证实,从定义上来说,我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无意识,但我深信不疑。有些事只能依赖信仰。但是我有证据,间接证据也算。
例子A,我痛恨早上起床,痛恨。没有一个黎明不是如此。我想把头埋进枕头,把被子拉过头顶盖住自己。冬天更别说了(父母为了省钱,把供暖温度调得很低,我们主要依靠厨房的煤油加热器取暖)。我窝在被子里,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享受着鼻尖和脸颊上的冰凉,但是让我只穿着内衣离开被窝,想想就绝望。
例子B,打盹儿没人能比得过我,要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有这个项目,我能拿冠军。我随时随地都能入睡,校车上眯五分钟(“眨了个眼”)或者晚上小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打了大盹儿”)。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的午休。无数个下午我都在沙发上,眼皮沉沉地耷拉着,呼吸清浅,暂时从这个世界抽离。
度假回来之后,我自发增加了睡眠的时间。康涅狄格州还是深冬,前院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显然短时间内我是没有办法和爸爸一起练习打棒球的。这样的天气让人只想深深埋进自己的小窝里。我们不是那种干什么都共同进退的一家人,或者有什么共同的信仰,主要集体活动就是看电视,除此之外家里没有什么事可干,写作业和看书也打发不了多少时间。我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妈妈最多能够忍受一个星期,之后作为母亲的责任感就不允许她继续纵容我了。
“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她说。周日早晨,她吵醒了我,虽然不是直接叫我起床,但是她用窸窸窣窣的行动达到了目的,她打开百叶窗,开始收拾我的房间。我突然意识到有个词语可以准确地形容妈妈——行动派。她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虽然她的批评是出于好意,但是她凭什么决定我需要睡多久?非洲的狮子一生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睡觉。就我所知,没人质疑它们是不是睡过头了,周日早晨它们睡得正熟的时候,也没人敢窸窸窣窣地吵醒它们。
“狮子每天睡二十个小时。”我说。
“是啊,但你又不是狮子。”她说。我早就料到她会这样回答,直截了当的现实虽然让我无话可说,但是偏离了重点——但是我刚刚睡醒,有点儿晕乎乎的。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我告诉她。这没什么稀奇的,算是我热爱睡觉的第三个证明,我做的梦是线性、有故事的美妙梦境,我不想清醒过来。刚刚的梦也很好,但是我不会跟妈妈多说。梦中,我们一家、暗影和其他怪物围坐在一起,妈妈一边给影子倒咖啡,一边跟它聊聊天气。我讲了个笑话,全家人都笑了,尤其是爸爸,他笑得停不下来,脸越来越红,眼睛里都是泪水,最后麦片从他的鼻子里喷出来,掉进了暗影的咖啡杯里。
“你不能浪费生命做梦。”妈妈说。
“我还有其他做梦的时机吗?”我问。
“算了。”妈妈说,她不喜欢长篇大论,也没有什么成熟的逻辑,她拉开了窗帘。
外面很冷,天空灰暗一片,不适合打棒球。我一直期待着什么时候能和爸爸一起在外面玩,于是想到唯一能练习的方式。我拿起手套,从走廊的衣柜里找出一只网球,然后走向地下室。日光灯管挂在低矮的天花板上,但是我没有感到头顶有压迫的感觉,因为我只有十岁,而且身高比同龄人矮。地面和墙面都是没有装饰过的水泥表面,对我来说正好。我从纸箱、旧折叠椅和其他杂物里清理出一条窄窄的通道,连接地下室两端,我用白色粉笔在对面墙上画了一个长方形,希望大小差不多等同于一个十二岁小孩的形体,然后开始投球。
冬季房子里很安静。地下室一片死寂,只有网球撞击水泥墙面反弹时发出的韵律声,我开始享受这种声音带给我的平静。第三天,爸爸终于下来了,我立刻感到担忧,我敢肯定他是来阻止我练习的,因为噪音让他和妈妈发疯。没想到他给了我一只弹力球,不但大小、形状跟棒球一样,球的表面还有凸起模仿棒球的缝线口。他说这比网球好,更接近真的棒球。我问他我的手势和技巧怎么样,希望他能指导我。他看着我投球,点点头。
“我看着没什么问题。”他说完之后就上楼了,留下了一阵短暂的沉默,我忍不住想,要是他能多说几句话,就能填满这段寂静。我满不在乎地抖抖肩,又面对着墙开始练习。
就这样过了几天,也可能是几周,我不清楚。当冬天慢慢过去的时候,我已经能把弹力球扔到任何我瞄准的位置。我急于向爸爸展示成果,刚刚出现雪融的迹象,我就拿出铲子去清理房前草坪上的雪。结果这比我想象的要难,铲子是为刮沥青设计的,不适合耙土。我已经把表层的坚冰弄破了,但是铲子前沿不断被草钩住。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试图清理出足够两个人接球的地方,直到胳膊因为劳累而发抖才不得不停下来,但我觉得足够了,第二天出太阳后刚好证实了我的想法,暴露在外的草坪被烤干,寒冬有了一丝春天的气息。
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戴着手套、拿着棒球在外面等候。他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我就迫不及待要投球给他看,我有很多问题——什么是二线球?怎么扔曲线球?你放下公文包需要多久?他进屋几分钟之后就出来了,而且也放下了公文包,但是他没戴棒球手套,而是拿了一个扁平的长方形纸盒——是投球网,天冷前我们一直没有机会用。爸爸拿出零件,快速把铁框架和网面组装好。
“看着投球板,好吗?”他说,“试试吧。”
那种小沉默又出现了,但是爸爸无意打破,我不知所措,退后一步,朝着投球板,抛出球。球击中板正中心弹回到我的手里,仿佛有一根绳子牵着。
“这比地下室的墙还要好,”爸爸说,“再扔几个我看看。”
我照做了,但心里并不情愿,也没有使多大的劲儿,相比之下,我在地下室就像是在扔炮弹。但是这个力道测试投球网刚刚好,对于爸爸来说也足够好。他最终点点头,摸摸我的头发,然后进屋了。
门还没关上,迪恩就冲出门来到除了雪的草坪上,他戴上手套张开手掌期待地看着我。
“轮到我了。”他说。
“我还没练习,而且雪都是我清扫的。”
“知道了,你要练多久?”
“我不知道,”我说,“你想玩接球吗?”
“接球?为什么?放着投球板不用,你要是不想……”
“我想用,”我打断他,“实际上我正在用。”我感到脸上一阵烧,有一种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揍迪恩一拳的冲动,也许想边哭边揍他吧。我转身面对着投球板,用十岁身体能使出的所有力量抛出了球,但是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球扔偏了,从球网的顶端擦过,掉进雪地里。迪恩一路笑着回了屋子。
“扔得好,王牌投球手!”他大喊一句。
于是,从深冬到开春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和投球板一起度过的,偶尔有特别大的暴风雨,我就去地下室对着墙壁进行击打练习。击球板可以同时练习接球和扔球。如果把球扔到球网顶端,弹回来的是变化球;扔到底端,弹回来上升球。迪恩就是这样练习的,他是球队的游击手,主要负责接球和守球。但是我的关注点在球网中心的长方形区域,这是我的好球带,除此之外,我不停朝四个角落扔球直到闭着眼睛也能击中目标。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坚持。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想跟爸爸一起练球,我怕他觉得我打得不够好;也许我只是想向哥哥证明我可以成为王牌投球手;也可能是因为对着投球板练习就像对着地下室的墙一样,重复抛出、弹回的球发出的韵律声让我感到平静。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很难解释,练习的节奏让我不再去考虑多余的事。迪恩宣称体育是一项战斗。他说人类千百年来都在互相残杀,进化决定了我们需要战斗,而体育,就是现代的一场没有血腥的战争替代品。这对迪恩来说是个了不起的见解,他甚至说得没错,但是天天如此过了几周之后,我投球的技术越来越娴熟,在我看来,这不是战斗,更像是舞蹈——头脑终于安静下来,像是消失了一样,只有身体舞动之美。
少年棒球联赛开始以后我的独训就结束了。我告诉新教练自己苦练投球,但还是被分派到了外野。赛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指定投球手生病了,我才有了一次上场展示训练成果的机会。我们对战的是哥哥的球队。虽然我觉得自己现在正需要这样一场比赛,但是还是感到紧张和害怕。两次不小心打中了击球手之后,我终于找回了投球的感觉。我想象自己站在前院的草地上,本垒板后面的接球手是家里的投球板,他的手套从好球带的一个角落移动到另一个角落,我一个都没有错过。
哥哥带头第二回合。我知道他不喜欢高远的投球,于是扔得又高又远。他看着一个球接一个球被打中,变得越来越焦虑。当他站在本垒板的边缘准备下一个球的时候,我就低低地把球扔在近处。他笨拙地向前跃身,但还是错过了球。第三次,他用球板狠狠砸了一下本垒板,一边走向球员席一边冲裁判大喊,一路上死死盯着我。
我们之间的闹剧在第四回合又上演了一遍,唯一的区别是三次投球的位置不同,以及迪恩气急败坏地下场前给了我更加不屑的眼神。之后他一直没有上场,直到最后一个回合,两个出局,一个二垒。我扔得很好,我们队领先一个本垒,但是只要哥哥能击中一个球,就能打成平局。他从球员席昂首阔步走上场,士气满满的样子,但我看到他在击球位做准备的时候,满脸通红,回避我的眼神。
第一个球低开出局,迪恩猛挥了一下球棒没有击中,他沉着冷静的伪装瓦解了,击球动作不再是往常那么游刃有余,变成了野蛮的挥杆。他大声咒骂了一句,好让爸爸妈妈都能听见。第二个球打飞了,迪恩若有所思地离开了击球位。当他最终看着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刚才的恼羞成怒,取而代之的是害怕。
我理解迪恩的心情。他今年十二岁,是在少年棒球联队打球的最后一年。他不应该跟自己的弟弟比赛,尤其是在输赢的关头。还记得我们一起抓落叶,我故意输给他,那时他脸上流露出的难以言喻的喜悦。其实,我现在只要把球扔到正中,他就能击中打成平局,然后露出骄傲的微笑。问题是,在抓落叶比赛中,我只要谎报数量就可以了,不用假装抓不到落叶。现在我必须故意失败,背弃整个冬天对着投球板和地下室的墙进行的辛苦训练。我必须清醒地告诉自己的身体要失常发挥,我必须不做自己。这我做不到。我只会一种扔球的方式,就是做到最好。如果哥哥能在外角击中球,我会第一个祝贺他;如果他打不到,活该!
他没有击中,意料之中。他挥杆力度过猛,跪在了地上,差点把自己甩出去。他保持跪的姿势瞪着投球手,棒球成功躲过了他凶狠的一击,安稳地落在手套中。比赛结束了。哥哥微微耸了耸肩,使劲把眼泪憋回去。然后站起来把球棒扔向围栏。他的爆发让场外顿时变得安静,于是当他转身鄙视着我时,大家都听见他下面说的话了。
“你只是运气好,怪胎。谁教你投球的?是跳舞的怪物吗?”
我不怎么辉煌的棒球生涯的终结就这样开始了。在一周的时间里,迪恩告诉了棒球联队大半的人说我相信怪物,不仅如此,还说怪物每晚都会拜访我的房间,穿着花裙子表演歌舞。在这之前,我和其他队员的关系友好,最差的也不过是漠不关心;现在,躲着我的人已经算是好的了,其他人都拿我当笑柄,甚至连我的队友都背着我嘲弄我。一个月之后,耻辱感和胸口的痛在我身上烙上了永久的烙印,我想清楚了:我不需要这些,我也不需要棒球了。我告诉妈妈肩膀疼,因为投球的次数太多了,疼倒是不假,但和扔球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她允许我缺席一次练习,然后是一次比赛,然后是另一场比赛,最终,我们心照不宣达成共识:我不会回棒球队了。
夏天终于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度过。当我厌倦了我家后院稀疏的小树林,便开始探索隔壁广阔的森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我们的邻居哈丁先生刻薄且吝啬,总是一副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架势,我觉得不是生活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他天生对世界充满了敌意,而他八十多年人生里,每一天都活出了真性情。他家屋后是枝叶茂密的森林和神秘所在,有一辆老旧生锈的农务器、一架手推犁和一个拖拉机的车壳,妈妈认为这是森林里很危险的信号,也是我不应该去森林里玩的原因。
下午晚些时候,我在禁忌森林深处发现了一个由矮石块堆成的很不寻常的正圆,圆圈正中的老树桩旁有一本书。这本书是谁的?它凭空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之前没有看见过?我没有多想,拿起书,背靠着树桩开始看书。
永恒之境的那个时期,有一个巨人,他有一颗巨大的心脏。
我打了个冷战,然后合上书。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困惑。那句话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头确实是有些奇怪,好像暗示故事已经开始了,接下来要讲的是续集,可实际上并不是,至少书封没有这样写。除此之外,那句话好像启动了什么,发出“咔嚓”一声,就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周围的世界变得昏暗,仿佛是快门按下去的一瞬间。这种感觉过于强烈,我观察四周,疑心是否出现了什么人或者其他变化,可一切似乎都安然无恙。斑驳的日光从树林间透下来,地面和我的脏牛仔裤上都是星星点点的亮光,树叶随着难以察觉的微风轻轻摇摆。我耸耸肩膀试图摆脱不安,再次翻开书。
这次,我已经不在意周围的一切消失在阅读之中,不久之后,连文字都慢慢不知所踪,只留下了文字所描述的世界。永恒之境。各种传说接踵而至,每次都带来一位不同的主人公。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永恒之境本身,那里神秘奇特,鲜活灵动。永恒之境里,万物皆有灵。树能说话,石头有感觉,甚至连天气都有意识。还有一位巨人,他拥有巨大的心脏,因此能够与血肉之躯、木头、石头、天空等一切事物交流。
光线渐渐变得暗淡,我停下不看了。白色的纸在昏暗中微微发亮,黑色的字母搅在一起,难分彼此。我抬起头,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太阳已经下山,森林笼罩在黄昏之中。蟋蟀的鸣声连绵起伏,萤火虫像点点星光笼罩在身边。我双腿僵直地站起来,有点儿头晕,回家的路漆黑一片,我有点儿冷,而且有点儿害怕。我不想穿过森林,于是决定抄近路回去,不过要经过哈丁先生家的后院。虽然有被发现的风险,但愿夜色能够掩护我。
离开了森林,我弓着腰在开阔的草地上奔跑,好像这样能让自己不那么显眼。眼看着要离开达哈丁先生家的地界,一个声音传出来。
“喂,旅行者。”
我愣在原地。黑暗中出现了一小束亮光,不是萤火虫,它一动也不动,一瞬间我以为是那束光在叫我,接着光点越来越亮,终于能够看清光源是后院一盏玻璃灯笼中的火焰。谢天谢地,站在那里的不是哈丁先生,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你好。”我回答道。
“你想干什么?”她问我,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我……什么也不是。”
“我不相信你什么也不是,”她说,“我也不相信你什么也没干,但你不愿意的话,不必告诉我。”
不知道是她的声音又或者是她的调笑,我突然感到松了一口气,不想跑了。
“你为什么叫我旅行者?”
“我觉得你像个旅行者,”她说,“要么你就是一只矮精灵。”
“一只矮精灵?”我忍住没笑出声,“我不是矮精灵,我是个小男孩。”
“矮精灵都这么说!现在我真的怀疑你到底是什么?到亮处来,让我看清楚。”
我走近后看清楚了她的样子,平静的眼神,苍白光滑的面孔。她棕色的头发凌乱地搭在肩上,其中夹杂着的几绺银丝在灯笼的照射下熠熠发光。她似乎既不老也不年轻。
“现在光线不是很好,”她说,“你的皮肤是绿色的吗?”
我终于忍不住咯咯笑了出来。
“我说的话很好笑吗?”
我马上停住。“没有,对不起。”
“没关系,”她说,“你可以笑,我不会介意的。”她微笑着,眼角的皱纹堆成了精灵翅膀上的纹路。“我叫艾瑟尔。”
“我是艾略特,住在隔壁。”
“很高兴见到你,艾略特。我想我见过你的父母,是企业家?”
“不是,是尚斯家。”
她哈哈大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但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她的笑声很美,充满感染力,像是从她的喉咙传来的一阵清亮的铃声。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人嘲笑你,不一定要生气,让他们笑好了。但我依然想知道原因。
“我说的话很好笑吗?”
她停下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我也不介意。”
艾瑟尔点点头,从椅子倾身向前。“企业家是个职业,做新的生意,”她解释,“是愿意冒险的人。所以,我们其实说的是一回事。你的父母经营鞋店,是吗?”
“是的。”说起父母,我想到自己该回家了。天已经完全黑了。妈妈该担心了,很快她就会打开后门,大声喊我的名字,直到我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希望艾瑟尔目睹我被召唤的一幕,但我也不想离开。最近我和家人没有过多的交谈,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交谈过,就好像房间里的氧气有限,说太多话会让我们窒息。
“你将来想成为企业家吗?”艾瑟尔问。
“不想。”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连自己都吓了一跳。一时间脑海中浮现出鞋店,不停焦虑的妈妈,还有爸爸每天早晨打完电话之后面红耳赤的样子。“但我想帮帮他们。”
“为什么?”
我想跟艾瑟尔解释,我试图从父母谈话内容中定位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找出解决方案,但每次都迷失在千头万绪的担忧之中——按揭贷款和个人担保、利率、员工周转、供应链。我耸起肩膀,埋着头,心底泛起绝望;我无法清晰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确定,”最终无奈回答,“也许我可以当个顾问?”
“那很厉害啊,”艾瑟尔说,“我敢打赌,你仅凭着观察父母就能学到各种宝贵的经验,将来你一定可以把学到的融会贯通,给其他企业家提出绝妙的建议。”
一瞬间,我的肩膀轻松了,绝望的感觉渐渐平息。但喉咙一阵紧,说不出话来。是的,我想说: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手里拿着什么?”艾瑟尔问,冲着我手里的书点点头。
我几乎忘了这回事。脑海中重新唤醒了永恒之境的记忆,我心里十分想回到那个地方。“关于一个地方,”我回答,“一个非常酷的地方。”
“啊,”艾瑟尔说,“那我不打扰你看书了。”
我抓着书的手紧了紧,好像怕被抢走。艾瑟尔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动作,她只是耐心地看着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这本书的确不是我的,于是我把书递给她。“我在森林里找到的,刚才正要借。”
“问谁借?”
“哈丁先生吧,我想应该是。”
这是我遇到艾瑟尔之后她第一次低下头,眼中的光彩变得暗淡。“哈丁先生去世了。”
我僵在原地。灯光外的黑暗变得危险、空旷。我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谁死了。我是不怎么喜欢哈丁先生,但他的死总让我觉得不舒服,而且,我感到有点儿愧疚,因为刚刚还庆幸他不在后院。
“我很抱歉。”
“我也是,”艾瑟尔说,“不过,他按自己的意愿,度过了漫长的一生,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他不欢迎我们在他的森林里玩。”
艾瑟尔点点头。“他不但看重自己的隐私,还是个混蛋。”看着我一脸震惊的样子她大笑。“这是事实,”她说,“但他是我的叔叔,无论怎样我都爱他。”艾瑟尔是哈丁先生的侄女这个事实让我更加震惊,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居然有着相同的基因。
“不管怎样,”她叹了口气继续说,“现在这片森林已经不是他的了,这里除了我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尽情地在森林里玩,你找到的那本书也属于你了。”
我胸口暖暖的,喉咙像是紧紧锁住了一样,但这次总算努力说了句话:“谢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艾瑟尔说,“你现在是不是该回家了,否则你父母会担心的。”
我点点头,挥挥手离开了。一堵破败的石墙分割了我们两家的院子,我走到墙边转身大喊:“跟你聊天很高兴。”
艾瑟尔在灯光中抬起手。“再见了,不是矮精灵的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