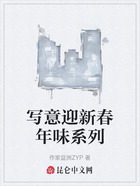
第128章 《耳子山铁匠铺的旧时光》
《耳子山铁匠铺的旧时光》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七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的父亲,一名乡村干部文书,常常会踏上前往耳子山铁匠铺的路,那是一段承载着许多回忆与故事的历程。
耳子山,一座并不高大却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小山。山脚下的铁匠铺,就像一颗古老而坚实的钉子,死死地钉在这片土地上,散发着炽热的气息。铁匠铺的房子是用石头和泥坯砌成的,屋顶上的黑瓦错落有致,岁月在上面留下了斑驳的痕迹。烟囱总是冒着淡淡的青烟,那是铁匠铺正在营业的信号。
我的父亲,身材高大而略显清瘦,常年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作为乡村干部文书,他的工作繁多而琐碎,从记录村里的大事小情,到调解邻里纠纷,每一件事都需要他用心去做。然而,他却总是抽出时间,徒步前往耳子山铁匠铺。
那铁匠铺里的铁匠,是一位名叫老铁头的老师傅。老铁头的脸就像被岁月的炉火烤过一样,黑红黑红的,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的眼睛却总是透着一股精明和坚定。他的上身总是光着膀子,露出结实的肌肉,那肌肉在炉火的映照下,像是用铜浇铸而成的。他的徒弟,一个年轻的后生,总是默默地在一旁递着工具,学习着打铁的手艺。
父亲去铁匠铺,大多是为了打锄头。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年代,锄头是农民们最得力的工具。村里的土地需要耕种,每家每户都离不开锄头。父亲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总是亲自去铁匠铺,确保打出的锄头质量上乘。
每次走进铁匠铺,父亲都会被那扑面而来的热浪所包围。老铁头看到父亲来了,总会咧开嘴笑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齿。“文书啊,又来打锄头啦?”老铁头的声音沙哑而有力。父亲也会笑着回应:“是啊,老铁头,这农忙时节快到了,得多准备些好锄头才行。”
打铁的过程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老铁头把一块铁坯放在炉火中,徒弟用力地拉着风箱。风箱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像是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炉火在风箱的鼓动下,越烧越旺,通红的火苗舔着铁坯。不一会儿,铁坯就被烧得通红,像是一颗燃烧的红心。
老铁头用铁钳夹出铁坯,放在铁砧上,然后举起手中的大铁锤。他的大铁锤就像一个威猛的将军,重重地砸在铁坯上。每一次砸下,都会溅起一片火星,那些火星就像夜空中的流星,四处飞溅。徒弟也会拿着小铁锤,配合着老铁头的节奏,轻轻地敲打。“叮叮当,叮叮当”,打铁的声音在铁匠铺里回荡,像是一首古老的乐章。
父亲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专注。他知道,这每一次的敲打,都是在塑造一件实用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也会和老铁头聊起村里的事情。
“老铁头啊,你知道吗?村里打算修一条灌溉渠,这可是个大工程啊。”父亲说道。
“修灌溉渠好啊,这庄稼就不怕缺水了。”老铁头一边打着铁,一边回应着。
“可是资金有点紧张,还得想办法筹集呢。”父亲皱着眉头说。
“文书,你是个有办法的人,肯定能解决的。”老铁头鼓励道。
在这样的交流中,锄头在老铁头的敲打下逐渐成型。老铁头会把锄头的刃口打得很锋利,然后再进行淬火。淬火是一门技术活,把烧红的锄头迅速放入水中,“哧啦”一声,冒出一股白色的水汽。经过淬火后的锄头,刃口更加坚硬。
父亲带着打好的锄头回到村里,村民们看到崭新的锄头,都充满了期待。在农忙时节,这些锄头在土地里欢快地舞动着。男人们扛着锄头走向田间,女人们则在后面提着水桶和种子。田野里,到处都是人们劳作的身影。
有一年,村里遭遇了旱灾。土地干裂,庄稼都快渴死了。父亲心急如焚,他带着村民们四处寻找水源。而那些在耳子山铁匠铺打造的锄头,此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村民们用锄头挖井,用锄头开辟新的灌溉渠道。虽然过程很艰难,但大家都没有放弃。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的形象在村民们心中更加高大了。他不仅仅是一个记录文书,更是一个带领大家克服困难的领导者。而耳子山铁匠铺的锄头,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希望象征。
父亲对打铁这门手艺,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常说:“打铁可不只是简单地把铁敲敲打打,这里面的学问可深了。”父亲认为,打铁是一门需要耐心、技巧和经验的手艺。每一次的锤击力度、角度,还有火候的掌握,都决定着最终成品的质量。就像做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他看着老铁头打铁,会感叹:“老铁头啊,你这手艺可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现在的年轻人啊,都不太愿意学这个了,真是可惜。”老铁头也会无奈地摇摇头说:“是啊,文书,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去外面挣大钱,谁还愿意守着这铁匠铺啊。”
父亲觉得,打铁手艺的传承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这门手艺代表着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它和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些经过铁匠精心打造的农具,是农民们在土地上劳作的好帮手,也是农耕文明的重要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的农具逐渐进入了村庄。拖拉机代替了牛耕,小型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也开始普及。耳子山铁匠铺的生意渐渐冷清了下来。老铁头的徒弟也离开了铁匠铺,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新的机会。
老铁头依然坚守着铁匠铺,他对父亲说:“文书啊,这时代变了,可我还是舍不得这铁匠铺啊。”父亲拍了拍老铁头的肩膀说:“老铁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你的手艺永远都在。”
再后来,父亲也因为年龄的原因,不再担任乡村干部文书的职务。他偶尔还会去耳子山看看,那铁匠铺依然还在,只是不再有往日的热闹。老铁头也老了,他的动作不再像以前那样敏捷,打铁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响亮。
然而,那些在七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父亲的心中。那耳子山铁匠铺的炉火,那“叮叮当”的打铁声,那一把把锋利的锄头,都成为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见证了村庄的发展,见证了人们的勤劳与坚韧。
这篇短篇回忆录以父亲在七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经常去耳子山铁匠铺打锄头为背景,展现了那个时代乡村的生活风貌。通过描述铁匠铺打铁的过程、父亲与铁匠的交流以及锄头在农业生产和应对旱灾中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同时,小说中加入了父亲对打铁手艺的看法,体现出他对这门传统手艺的敬意以及对其传承面临挑战的担忧。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农具的普及,铁匠铺的衰落也象征着时代的变迁。但那段旧时光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成为了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勤劳、坚韧以及乡村生活的质朴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