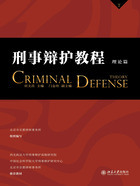
二、控辩关系
刑事辩护以刑事控诉为前提,没有控诉即不存在辩护。[55]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共同形成了辩方。随着当事人主义日趋植入我国刑事诉讼过程,辩护律师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辩护律师的设置是平衡诉讼结构的需要。因为控方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表,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忽视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的情况,这时候辩护律师可以把收集到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提交给法庭,从与控方相反的立场出发主张事实与法律适用,从而避免出现控方一方独大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辩护律师的加入,加强辩方的力量,使控辩双方的武器平等,而只有在控辩双方平衡的情况下,庭审中的两造对抗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合理配置控辩双方的权利,赋予辩护方完整的主体性权利以及充分的防御和对抗的机会,使控辩双方在“平等武装”和“平等保护”的前提下展开攻防活动日益受到重视。但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的控辩关系一度呈现出控方的诉讼地位、权利相对强势,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权利相对弱势的态势。与《刑事诉讼法》几次修改的内容相适应,我国的控辩关系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一)《刑事诉讼法(1996)》
我国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过一次全面修订,在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的设计上,力图借鉴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一些成功经验,通过对质证程序的相关规定来改造控辩双方的地位,以求营造出一种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环境。但在实践中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侦查阶段,律师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律师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刑事诉讼法(1996)》第96条规定了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虽然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但在该阶段律师的地位不是“辩护人”。并且律师进入侦查程序后的权利范围只能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除此之外,律师不能进行其他的诉讼防御行为。
二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方的权利有限且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刑事诉讼法(1996)》第33条规定,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有权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接受委托的辩护律师可以通过以下活动来行使辩护权:(1)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2)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3)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4)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是,在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这些权利往往无法充分地得以行使,例如对于控方收集掌握的证据材料很难获取,在调查取证时,需要经过同意才能进行收集等。
三是在审判阶段,控辩双方的地位、“武器”失衡。由于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不平等,导致在审判中控辩双方获得的信息不对称。这样,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就会被大大地弱化,辩护律师想要通过提出事实和证据来影响法官的裁判就变得尤为困难。[56]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辩护和审判是三大基本职能。控辩平衡是基于这三大基本职能,从诉讼构造设计的角度出发提出的理论。有人狭隘地把控辩平衡理解为在庭审中赋予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但如果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没有充分地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独立的调查权,那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只会起到走过场的作用。事实上,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都应予以体现。首先,是控方的侦查权与辩方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平衡;其次,是控方的讯问权与被告人的沉默权、律师在场权的平衡;再次,是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对抗机会的均等。[57]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曾就“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在2010—2011年进行过专题调研,调研发现,刑事辩护律师的法定权利落实不到位,救济渠道不通畅,司法机关对律师辩护意见不重视,是造成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比例过低的主要原因。[58]
(二)《刑事诉讼法(2012)》
2012年,我国再一次全面修订《刑事诉讼法》,此次修订对控辩平衡的理念进行了进一步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刑事诉讼法(2012)》第3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说明从侦查阶段开始,律师可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诉讼,即确立了刑事辩护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此项规定将委托辩护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解决了侦查阶段律师身份不明的问题。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侦查活动起到外部监督和制约作用,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刑事诉讼法(2012)》第35条规定辩护人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结合第49条规定的“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该条确立了辩方不承担举证的责任,由控方对被告人有罪承担举证责任。
3.《刑事诉讼法(2012)》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等“三证”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且在会见时不被监听,这对保证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效的沟通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
4.《刑事诉讼法(2012)》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这一规定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查阅案件材料的范围。
5.《刑事诉讼法(2012)》第39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调取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刑事诉讼法(2012)》的颁布与施行使得辩护律师在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方面的诉讼权利得到强化,与《律师法(2012)》有效衔接,控辩平衡的现代司法理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彰显,在立法上无疑对我国法治的发展起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落实到执法上,实践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发表辩护意见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三)《刑事诉讼法(2018)》
2018年年底,为了与《监察法》衔接,配合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的调整,配合监察委承担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的改革,再一次全面修订了《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虽然承认了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调查所获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但是在长达6个月的监察委的留置期间,律师无法介入,不能会见,要一直到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才能会见。此次修改无疑限缩了律师辩护权。
(四)对抗,从形式到冲突再到理性的演进
在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同阶段,控辩双方的对抗关系也处于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之中。在律师制度恢复初期,控辩双方曾经处于一种形式对抗的状态之中,属于形式上对抗、实质上配合的关系。在这种形式对抗状态下,辩护律师实质上是与控方一道配合法官办案,并非在真正行使辩护权。辩护律师的参与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实施的辩护也不可能是有效的辩护。
后来,随着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律师事务所由公办向民营的转制,在律师职能的独立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控辩关系又因矫枉过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由形式对抗转向冲突性对抗,导致庭上庭下双方交恶的非理性冲突的后果。形式对抗与冲突性对抗都是违背刑事诉讼规律的控辩关系,是中国辩护制度不成熟的体现。目前,随着庭审方式的不断改进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正在向理性对抗的正常化状态转变。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公诉人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对抗性增强,但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视野下,控辩双方应以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为目标,加强交流互动,促进协商合作。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职业道德要求,二者应当互相尊重,形成“对抗而不对立、交锋而不交恶”的理性对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