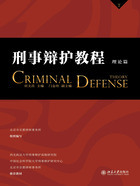
二、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两大基本关系
决定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内容的两大基本关系:一是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关系,二是辩护律师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这两大基本关系的价值排序几乎可以解答所有司法实践中出现有关职业伦理问题的争论。在应然层面上,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关系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维护的信赖关系,这是辩护律师角色以及辩护制度存在的基础。与被追诉人的信赖关系是架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基本逻辑。
(一)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关系
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关系是指应然意义上的信赖关系,也可从义务视角称之为信赖义务。
辩护权要实现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防御权,辩护人的权利源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辩护律师的信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因此,设定辩护义务,在一般情况下不得与维护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相矛盾,换言之,维护与被追诉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是第一辩护义务,法律上也不应设定有伤及信赖关系的义务。比如公民有揭发犯罪的义务,但是对辩护律师就不应设定揭发委托人的义务。一般法治国家不但不设定辩护律师有此义务,还在制度上确立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证权,这样才不至于让辩护律师陷入自相矛盾的角色之中。一旦辩护律师的法定义务中有伤及信赖关系的内容,就会从根基上伤及律师角色,妨碍辩护义务的履行,从而导致“刑事辩护”成为“形式辩护”。
在辩护过程中,除法律明文规定的基于存在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需要保护人身及重大公共利益免于危险的例外,任何有损辩护人与委托人之间信赖关系的行为都不被律师职业伦理所接受。试想,当委托人对辩护人处于不信任的状态,当辩护人对委托人实施了揭发,还有什么正当的逻辑和理由替当事人尽职辩护。辩护人与被追诉人之间丧失信赖关系,并且该信赖关系难以恢复时,辩护律师不应固执地维系这种委托关系,这是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基本点。
(二)辩护律师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辩护律师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体现在义务层面是指其实现社会正义的义务,简称公法义务。
存在这一关系是基于辩护律师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适用的是公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有关,解决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因此,“实现社会正义”的公法义务要求辩护律师担负公益性社会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赋予刑辩律师享有独立于被追诉人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律师在法庭审判中享有辩护权,等等。这些一般公民不享有的权利彰显了刑辩律师在法律事务中的专业地位,因此,赋予刑辩律师必须承担社会所期待的“公共责任”,是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体现,也是世界诸多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比如日本《律师法》第1条第1款把刑事律师和民事律师的共同使命规定为“律师的使命是,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比如,据大判昭和5年(1930年)2月7日《刑集》第9卷第51页记载,辩护人阻止真正的犯人去自首,继续为替身犯人进行辩护活动,结果被认定为隐匿罪犯罪。[71]可见,虽然从未有哪个国家会赋予辩护人积极揭发犯罪的义务,但也不容忍律师用积极作为的方式共谋犯罪,要求律师承担一定的实现社会正义的公法义务。
我国《律师法(2017)》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律师的使命为“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我国《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2017)》第7条也表达了相应的意思:“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可见我国相关立法规定的律师使命包括维护当事人利益和承担公法义务两方面,且后者被更加强调。在我国依据长期以来积累的认识形成的对律师“公共责任”的期待是根深蒂固的,在大力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今天,律师的“公共责任”更加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