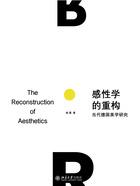
第四节
贡献与不足
由此,泽尔建立起了一个既有清晰立场,又有巨大开放性,能最大限度地涵盖迄今为止的所有审美现象、艺术革新,并且应对潜在挑战的美学体系;为当代美学研究在应对来自理论革新与艺术革新的双重挑战时,又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泽尔的写作,更多地专注于问题本身的提出、界定、分析与澄清,没有豪言壮语,不过多地涉及理论、流派、主义所带来的枝蔓,整个文本干干净净,有着最小限度的引用,直接进入主题,说清楚,说明白。这也是导致这样一本高密度的书却如此之薄的一个原因。
当然,它也绝不是一个天衣无缝的体系。比如说:对显现的强调,对感性基础的强调,依然与康德传统一脉相承地把非感性领域比如哲学研究、数学计算中偶尔获得的高度愉悦排除在审美视野之外;即使就感性经验而言,泽尔也依然是更多地集中在视觉与听觉经验上来谈审美显现,至于味觉、触觉是否可以成功演绎“显象间游戏”,泽尔并没有做出说明,倒是在谈到“杂音”的时候,在注脚中说到只有听觉与视觉可以欣赏杂音,其他感官对杂音只会拒斥。那么,进一步推理,这种旨在彰显不确定性的显现事件,对于触觉与味觉来说,是否可以忍耐并且“逗留”?对审美经验所凸显的人类存在以及世界的“不可规定性”的强调,其意义何在?通过显现,我们除了强化自己的在场感、时间意识、自我意识,此外还能实现什么?对于安慰我们必死的宿命,单单是瓦雷里寓言中对有死生活每个瞬间丰富性的赞美就足够吗?我们如何获得足够支撑来注视我们的当下?是否叔本华的那种借助审美超越有死存在的一厢情愿中,就真的没有对艺术价值的积极揭示?投身还是忘却?注视还是超越?回归当下还是倾向永恒?这些似乎会成为长久的对立。
当然,这些并不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身限度的美学理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作者本人也明确表示,建立一个大而全的体系并非他的本义,他的努力是建立一座桥梁,向各种可能性敞开,朝向“审美意识的风景深处”[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