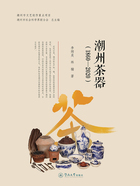
第一节
汕头开埠与潮瓷运销
1840年,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故我们通常把鸦片战争作为划分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860年汕头对外通商,洋货进入,同时带动地方土产的输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促使汕头成为近代埠市。民国时期,汕头已形成近代城市化格局,成为韩江、榕江、练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
潮瓷行业顺应时代发展,逐步在汕头埠立足。
一、汕头开埠
1858年,清廷被迫与美、俄、英、法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开辟潮州府城口为通商口岸。 同年,英国在汕头设立领事馆,汕头也开办了德记洋行和怡和洋行。随后,德、日、法、美、俄等国侵略者接踵而至。
同年,英国在汕头设立领事馆,汕头也开办了德记洋行和怡和洋行。随后,德、日、法、美、俄等国侵略者接踵而至。 自此,岭东门户被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
自此,岭东门户被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
在清政府被迫开放汕头为通商口岸后,外国人又在妈屿岛上设立由洋税务司把持的潮州新关,后称为“潮海关”,又称“洋关” 。旧有的税关则改称“常关”,只征收国内商货的税款,以区别新设的海关
。旧有的税关则改称“常关”,只征收国内商货的税款,以区别新设的海关 。
。
潮州府汕头港对外通商后,汕头逐渐代替潮州城区成为粤东的商业中心。《潮州志》 载:
载:
其时欧人航海来华贸易者日众,濒海得风气之先,新商业重心之沙汕头爰告崛起。洋船昔之泊于樟林港者,亦转而泊于沙汕头,人烟辐辏,浮积加广,交通既便,遂取郡城商业地位而代之。
加上洋轮码头建立,其吞吐量迅速增长,汕头港成为粤东地区的对外门户。
汕头为华南第二商港,贸易地方由海道可通厦门,台湾,福州,上海,青岛,烟台,天津,大连等处,向西南可及香港,澳门,广州,海口,海防,西贡,曼谷,新加坡,槟榔屿,日里,仰光,及南洋群岛各埠,内通各县及闽西八属,赣南七属,对外贸易国家(和地区)为暹罗,(中国)香港,南洋群岛,安南,日本,(中国)台湾,与英,美,俄,德,瑞典等,……汕头每年贸易总额达一万万元以上,……由汕头输出外国者为纸花,生油,陶瓷器,抽纱,腌菜,麻苎,土酒,生叶果,……由汕头轮往各省者则以纸,糖,土布,烟丝,麻苎品,陶瓷器,果实,锡薄等。
这一时期,与广东毗邻的福建,其港口福州和厦门的主要输出品均从手工制品转向农副产品,瓷器的出口量远远落后于其他物品,仅有广茂隆、泰祥、益安三家专门“办理漳泉两府所属之石码、同安、德化出场的陶瓷器,向南洋及(中国)台湾等地输出”的“碗郊”。 德化瓷商办理陶瓷出口业务等待时间变长,产品出口受到限制。一些德化瓷商看到潮州陶瓷产品通过汕头港源源不断销往海外,为谋求生计,也不惜远路将产品运往汕头,再进行外销,以扩大出口盈利。
德化瓷商办理陶瓷出口业务等待时间变长,产品出口受到限制。一些德化瓷商看到潮州陶瓷产品通过汕头港源源不断销往海外,为谋求生计,也不惜远路将产品运往汕头,再进行外销,以扩大出口盈利。
可见此时,位于韩江出海口的汕头埠已初具规模,逐渐成为粤东、闽西、赣南商业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当时,经汕头外销的土特产等货物中,潮州陶瓷占很大的比例。潮州属下的枫溪、高陂、九村和府城内是潮州陶瓷的主产地,其外销的产品各具特色:高陂、九村以青花瓷为主;府城内以釉上五彩为主;而枫溪的陶瓷产品主要有大窑五彩、青花、色釉和雕塑瓷等。
表1-1为1865—1930年汕头海关对陶瓷的外销额统计。
表1-1 1865—1930年汕头口岸出口外洋陶瓷统计表

注:表中的陶器主要为细陶,粗瓷主要为高陂粗碗。
根据表中数据:1915年陶器出口量达151 304司马担,1920年粗瓷出口量达165 799司马担,可知1920年之后潮州瓷器外销量高于陶器,说明高陂瓷业改良获得成功,产品生产规模提升。加之枫溪使用飞天燕瓷土,有效地提高了细瓷的质量,扩大了生产规模,潮州地区瓷器总体的生产规模和外销数量均得到大幅提升。
汕头开埠,无疑为潮瓷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渠道。在欧风东渐与文明商战之秋,枫溪窑业的有识之士接受新观念,认识到商业竞争的重要意义,合力振兴枫溪陶瓷业。如1912年,吴源兴、章安顺、吴清泉、吴宝合、吴仁记、吴乔钿、吴道记、章永成堂、吴龙记、吴发利、章瑞兄、章协利、吴安顺、吴坤记、吴益记、吴长记、吴德记、章娘保18家窑厂,合力共创“新兴埠股份”27份,集资建筑老窑1条,新窑1条,并窑厝29间,除议明“各股份日后如有更易,不得赔当出股外人,庶不负创业诸人”外,还议明“缶出入窑无论经何号地方经过,须自将路道修通,否则,如有撞破系该号自误”(见图1-1)。合股书体现潮州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对西方近代化的先进工商业先知先觉。枫溪陶瓷业者怀揣着“实业报国”的情怀,以规范管理组建合股经营,体现了同心合力的创业精神。此外,由合股书也可知当时西塘乡人已到枫溪乡合资创业。

图1-1 合股书(局部)
二、潮瓷运销方式的转变
汕头对外通商后,火轮的出现促进了潮瓷销量的提高,也改变了潮瓷的运销格局。潮瓷依靠便利的交通运输,以汕头港为枢纽,销售至海内外各个地区。
(一)交通方式的变革
潮州府汕头港对外通商后,英国印度支那航业公司、英商中国航业公司、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和德国雷特公司等远洋航运公司的船舶相继出入汕头港。 此后,帆船逐渐被火轮代替,商人通过轮船经营远洋和近海运输,往来船舶日益增多。依据潮海关档案记录统计,1870—1930年,汕头港往来外洋海轮从400艘次渐增至近4 000艘次。
此后,帆船逐渐被火轮代替,商人通过轮船经营远洋和近海运输,往来船舶日益增多。依据潮海关档案记录统计,1870—1930年,汕头港往来外洋海轮从400艘次渐增至近4 000艘次。 到20世纪20年代,每年有四五百艘中外汽船在汕头港停泊,总货运量约20万吨。
到20世纪20年代,每年有四五百艘中外汽船在汕头港停泊,总货运量约20万吨。
近代汕头港的兴起促进潮瓷的发展。汽轮的到来,使汕头与本国沿岸各省及南洋群岛交通日渐便捷。以汕头至南洋的海上船程为例,采用木帆船需要一个月,采用汽轮则只需一周。显然,汽轮的出现,不仅活跃了临港乡镇的经济,还发展了陶瓷手工外销产业。《潮州志》载:“适近代南洋交通畅达,日用粗瓷大旺”,“潮州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外,运销出口尤多,计至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中国)香港及暹罗、安南、南洋群岛等处”。
枫溪与汕头港相距仅30多公里,是传统陶瓷产地,枫溪瓷业正是搭上汕头港这一顺风车才得以发展的。在海内外市场的刺激下,枫溪兴建了几十座平地龙窑。茶器作为枫溪日用瓷一大品种,也得到迅速发展。
同时,1906年通车的潮汕铁路,对瓷土运输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飞天燕瓷土矿位于桥东东津,开采后由航船运输到韩江对岸北堤头的潮汕铁路站(今凤山军营),而后通过火车运至枫溪站,再由人工两轮板车运至各作坊和涂店 。这种运输方式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促进了薄胎高温瓷器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提高了瓷质茶器胎釉的质量。
。这种运输方式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促进了薄胎高温瓷器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提高了瓷质茶器胎釉的质量。
(二)运销格局的转变
汕头开埠前,本地的陶瓷商行都集中在潮州府城。除西郊的枫溪外,大埔高陂和饶平九村生产的陶瓷也通过韩江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运至府城东平路、竹木门一带经营陶瓷的碗行。但是,由于汕头埠位于韩江、榕江、练江这三条潮汕地区主要内陆航道汇聚处,又具备良好的深水港条件,地理条件比潮州府城更加优越,所以汕头海关开关之后,很快便取代了潮州府城在韩江流域的运销中心地位。
潮汕各瓷区所产陶瓷,或由汕头转口运至广州、上海、香港等商埠,或直接从汕头港运至新加坡、槟城,再转至东南亚各国。原枫溪、高陂的陶瓷业者,部分资本较为优裕的,直接在汕头开设商行货栈,其余则成为汕头的供货商。
汕头埠繁荣的商务往来促进了潮瓷产销量的发展。民国初期,潮瓷经营最高峰时,“潮梅(潮安枫溪及梅县、大埔高陂等)瓷器出产,经汕头出口者,每年值500万元,枫溪瓷为最多” 。
。
下面对枫溪、高陂、九村三大陶瓷产区产品的运销方式进行介绍。
枫溪位于潮州府城西郊,陶瓷产品主要从几个码头运出。陶器粗缶在三利溪长美码头装船,瓷器细缶则由三利溪枫溪宫前洋装船,直往汕头港。 也有一些外销瓷器从枫溪肩挑运送至府城下水门外或上埔的韩江码头上船,运至澄海东里樟林港装上外轮。当时,销往欧洲的货物俗称“红毛货”,销往东南亚的货物俗称“番仔货”。枫溪瓷器用高约1.5米、直径1米的大竹筐包装。装瓷时,工人在竹筐里先垫上稻草,然后装上一层瓷器,撒上一层谷壳,谷壳上面再加一层稻草,再装上第二层瓷器……直至瓷器装满,再用竹匾盖上,并以竹绳缝封。竹筐顶上编有两个半圆系扣,可穿上扁担,供两个人抬运装船。
也有一些外销瓷器从枫溪肩挑运送至府城下水门外或上埔的韩江码头上船,运至澄海东里樟林港装上外轮。当时,销往欧洲的货物俗称“红毛货”,销往东南亚的货物俗称“番仔货”。枫溪瓷器用高约1.5米、直径1米的大竹筐包装。装瓷时,工人在竹筐里先垫上稻草,然后装上一层瓷器,撒上一层谷壳,谷壳上面再加一层稻草,再装上第二层瓷器……直至瓷器装满,再用竹匾盖上,并以竹绳缝封。竹筐顶上编有两个半圆系扣,可穿上扁担,供两个人抬运装船。 枫溪宫前洋码头和长美码头停泊着往来于汕头、揭阳的木船,船身窄长,俗称“枫溪条”。这种船长7~8米,宽约1.5米,只可并排放两个大竹筐。船头船尾各一船工划撑,顺着溪流行驶,较为省力。一般为货物装船后,待退潮随流行驶至玉窖,暂宿一夜,次日另一次退潮时,继续行驶。船经中离溪后从举丁关到达汕头港,也可从揭阳枫口经榕江到达汕头港,全程需两天。枫溪条载货到达汕头后,停靠在西港船坞。西港附近的太古港专门停靠外国轮船,这里的火轮直接到达香港、广州、上海等地。
枫溪宫前洋码头和长美码头停泊着往来于汕头、揭阳的木船,船身窄长,俗称“枫溪条”。这种船长7~8米,宽约1.5米,只可并排放两个大竹筐。船头船尾各一船工划撑,顺着溪流行驶,较为省力。一般为货物装船后,待退潮随流行驶至玉窖,暂宿一夜,次日另一次退潮时,继续行驶。船经中离溪后从举丁关到达汕头港,也可从揭阳枫口经榕江到达汕头港,全程需两天。枫溪条载货到达汕头后,停靠在西港船坞。西港附近的太古港专门停靠外国轮船,这里的火轮直接到达香港、广州、上海等地。 枫溪条装载瓷器,或者通过俗称“大五肚”(有五大隔板的大木船)的驳船装上外轮出洋,或者卸入汕头太古、怡华等商行的货栈,等候中转其他地方。
枫溪条装载瓷器,或者通过俗称“大五肚”(有五大隔板的大木船)的驳船装上外轮出洋,或者卸入汕头太古、怡华等商行的货栈,等候中转其他地方。
高陂及其毗邻的各山区乡镇蕴藏大量优质瓷土矿,瓷器生产历史悠久,是大埔、饶平一带陶瓷产品的集散地。高陂位于韩江中游,背靠大山,水路交通极其便利,溯江而上可达江西、福建,顺流而下直抵潮州、汕头。陶瓷商人利用高陂临江的水上交通优势,开设碗行、瓷庄,发展瓷业经营。高陂瓷商大部分将产品用小船运往东陇,在东关税厂付了常关税之后,用小船将瓷器运往澄海樟林港,不经海关直接装上帆船,运往中国沿海各地和法属的印度支那。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的瓷器通过汕头港的轮船运载出口。
九村位于饶平北部山区,对外交通不便,但与高陂相距甚近,只有20多公里山路的距离。一直以来,这一段山路上存在一个苦力行当——挑夫,俗称“担高陂”。挑夫们把九村生产的陶瓷产品挑运到高陂,又将高陂的土纸、油盐挑回九村,非常辛苦。高陂的瓷商收购九村陶瓷之后,将其与临近乡镇的产品一起混合销售,九村瓷器就这样通过高陂输出。
三、海内外市场促进下的潮州茶器
汕头开埠后,由于交通条件改善,潮州的东南亚移民人数迅速增加,中国与南洋商事也快速活跃。《新加坡风土记》载,“华人住坡,户口最难详确。光绪七年(1881)英人所刊户口册云,……潮州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占新加坡华人总数86 766的26.1%。 《潮海关史料汇编》统计,1873—1934年汕头港出国旅客人次为5 348 061,回国人次为4 223 813。另1936年《侨务月报》载“有汕头出口侨民计298万余人,归国人口侨民计146万余人”,即1904—1935年,从汕头港乘轮船移居海外谋生的潮人达300万人次,其中很大一部分移居泰国。移民潮催生了一个人口量巨大的海外潮人社会,这也是潮州陶瓷外销的大市场。
《潮海关史料汇编》统计,1873—1934年汕头港出国旅客人次为5 348 061,回国人次为4 223 813。另1936年《侨务月报》载“有汕头出口侨民计298万余人,归国人口侨民计146万余人”,即1904—1935年,从汕头港乘轮船移居海外谋生的潮人达300万人次,其中很大一部分移居泰国。移民潮催生了一个人口量巨大的海外潮人社会,这也是潮州陶瓷外销的大市场。
潮州是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境内的凤凰山乌岽顶海拔一千多米,终年烟雾缭绕,盛产茶叶。《清朝野史大观》载:“中国讲究烹茶,以闽南之汀、泉、漳三府,粤之潮州府工夫茶为最。”茶器是泡茶的必备之物,潮州人习惯使用的茶器为陶瓷器皿。潮人对工夫茶具极为讲究,近代富贵人家崇尚使用宜兴产的紫砂茶具(宜兴位于江苏,故也称其茶具为苏罐),一般人家则多使用本地产品。
潮州工夫茶器一般崇尚“壶要朱、杯要白”,即壶以朱红色为佳,杯以白瓷(也称白玉令)为主。茶具为潮州人家居必备的器物,人们对其品质的要求依家庭情况而定。潮州工夫茶器中最基本的壶、杯、锅、炉被称为“工夫茶具四宝”(见图1-2)。
这些茶具及饮茶习俗也被移民带到移民地,代代沿袭,潮州文化随之在东南亚传播。东南亚市场的茶具、咖啡具也成为潮瓷外销的主要品种。
这一时期,潮州茶器产品在本地市场也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

图1-2 工夫茶具四宝
一方面,在海外事业有成的潮人,怀着回报家乡之心,将赚到的钱寄回家乡置产立祠,竞相“起大厝、建祠堂”。潮州兴起宗族祠堂及私人府第的建设,其中包括传统中式庭院,如四点金、下山虎、驷马拖车。“潮州厝,皇宫起”这句俗话道出了潮州民居建筑宏伟的规模和豪华的装饰。这一时期的知名建筑有建于同治九年(1870)的从熙公祠,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己略黄公祠,修于清末的甲第巷资政第以及建于宣统二年(1910)的澄海陈慈黉故居等。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民居、庙宇的兴建,饮茶之风盛行,使潮州进入了“同光中兴”的繁荣时期,其时陶瓷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潮州茶器的发展。
受西方文明影响,潮州、汕头本地很多新兴建筑、家具都使用洋花造型装饰,西式风格的茶具、餐具等日用器一度风靡于上流社会,引得枫溪陶瓷业者争相模仿。枫溪所生产的仿洋陶瓷器,不仅在枫溪本地大受欢迎,还销往中国香港及南洋等地。
另一方面,经过明、清两代的积淀,近代潮州民间文化习俗已趋成熟,给茶器带来了发展的良机。“游神赛会”和各种宗族祭祀活动,各有不同的文化风俗,但有一点相同,就是都必须循例祭拜祖宗。在祭拜祖宗时,需要一套精美的敬茶器具,以表示对先祖的尊敬、感恩。此外,祭祀过后,一般都会有亲友聚会,主人会在宴会前后冲泡工夫茶,供客人饮用。
庭园式家居的涌现和民风民俗的兴盛,推动工夫茶的再次兴起,怀古的工夫茶饮风靡于社会各阶层。金武祥在《海珠边琐》中写到:“潮州人茗饮喜小壶,故粤中伪造孟臣、逸公小壶,触目皆是。”富有人家、士大夫对茶具的选用十分讲究,连横在《茗谈》中说:“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
在市场的作用下,枫溪陶瓷业者于传统壶、杯、锅、炉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工夫茶具的种类,并在实用性和观赏性上加以创新。茶船(茶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综合了茶盘与水钵的优势,合二为一,既具有盛放废弃渣水的功能,又大方美观。长腹盖罐壶、长腹执壶虽与水钵一样都具有储水的功能,但长腹盖罐壶腹部一般有铜质水龙头装置控制水流出,而倾倒长腹执壶便可出水,相比之下,水钵需借助勺子舀水,略显烦琐。新出现的茶船、长腹盖罐壶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茶盘、水钵,而是并存,供茶客自由选择使用。
此外,潮阳流溪潮盛号生产的红泥炉以书卷对联作装饰,联语为“潮语忠言炉非假货,盛情美意茶是真夷”。联语内容对仗风趣,既是产品广告,又透露出当时崇尚饮用武夷茶的饮茶习惯。这种红泥小炉设计巧妙,与薄锅仔完美配套。
清后期,工夫茶成为海内外潮人不可或缺的日常饮品,工夫茶的风行带动了工夫茶器的需求,其他地区的陶瓷业者也纷纷加入了竞争行列,茶器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潮州茶器出现了系列化,进一步推动了饮用工夫茶的风潮。这一时期,枫溪大路顶红罐铺内制壶艺人吴英武因生产孟臣款造型的小茶罐而知名,被业界称为“吴孟臣”,他与族人创办的“源兴号”手拉朱泥壶一直延续至今,是枫溪朱泥壶的著名品牌。
一泡好茶,除了精致齐全的茶具,也离不开好水。潮人饮茶首选活泉水,如西湖处女泉泉水。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1864—1912)在潮期间曾作《潮州春思》一诗:“曲院春风啜茗天,竹炉榄炭手亲煎。小砂壶㵸新鹪嘴,来试湖山处女泉。”此诗描绘了春日在潮州西湖处女泉边烹饮工夫茶的情景。王玉岭先生创作的品茗图表现的也是这一景象。井水也是工夫茶客的烹茗源泉之一。美中不足的是,井水虽有消热解毒的功效(中医认为),但杂质较多,故茶客大多用水钵或长腹盖罐壶储水,过滤杂质后再使用(现存茶具传世品中,也以水钵数量最多);也有一些茶客以陶缸储水,缸内装木火炭、韩江溪沙等用来过滤,缸下腹装设龙头取水(待一定时间后再将溪沙取出,漂洗后可继续使用)。
清末民初,潮州瓷质茶具多彩绘五彩、蓝彩,纹饰以山水、人物、花鸟为主,彩瓷艺人多为一专多能的画师,他们将传统国画的笔法、构图、民间优秀的工艺图案以及地方戏剧的装饰特点融入彩瓷彩绘,使得潮州瓷质茶器的彩绘技法更为精细,构图更为完整,题材也更为广泛。题材有人物、花鸟、虫鱼等,也有象征福气、长寿、品格高洁的蝙蝠、团鹤、莲花等;主要的画法有工笔、意笔、兼工带写等,无不体现出潮州茶器独特的艺术个性。
陶质茶器是工夫茶的主角,其中朱泥壶最为知名。陶质茶器的生产集中于枫溪大路顶及西塘一带,源兴、安顺等多家作坊均有制作。产品造型较清早中期丰富,有传统工夫茶小壶如水平壶、梨形壶、文旦壶、思亭壶、美人肩壶等;还有传统的直腹(形如洋铁皮桶,俗称“洋桶壶”)软提梁壶及配以多孔茶胆球形壶的贡局款软提梁壶(俗称“寿星壶”)。
近代汕头港对外通商后,潮瓷营销中心从潮州府城逐步迁往汕头埠。那里便利的商品贸易、海运、结算等,促进了潮州茶器产品的外销。随着大量潮人下南洋,饮茶习惯也被带至当地,带动了茶器、咖啡器具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潮人在海外经营事业有成后,又回到家乡“起大厝、建祠堂”,庭园式家居的出现和民风民俗的兴盛,也再次推动工夫茶的兴起,促进茶器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潮州茶器因其精美而独特的地方特色广受海内外市场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