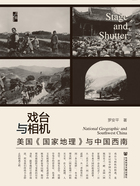
纸上之行:地理、旅行与民族志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刊物,创刊于1888年,至今已有130余年历史。在官方网站上,其宣传语为:
国家地理学会是全球性的非营利科学和教育机构,自1888年以来,通过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探索者、摄影师和电影制作者们,生产极具开创性的故事,致力于激励人们探索和关爱我们的星球。我们的黄色边框提供了一扇通向地球以及地球之外的大门。[24]
迄今为止,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已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发行,这本有着亮黄色边框的杂志,在大众文化时代确实有极大的影响力。当然,在跨文明接触与交流中,它必然引发不同的观感与评说,盛赞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前者如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n Howard Taft),他的一段话被《国家地理》杂志反复引用。
凡是阅读过《国家地理》的人都明白这份杂志的成功何在。它不会为了迎合受众口味而热衷于揭发丑闻或卷入性话题——这是如今很多杂志提高发行量的伎俩。杂志将努力的方向聚焦于地理问题,无论是地形、环境、面积与气候,还是人类自身的丰富差异性,以及人类历史如何受地理环境制约与影响,这些广泛的地理议题,都是学会与杂志研究的着力点。[25]
而两位人类学家凯瑟琳·卢茨和简·柯林斯却在细读《国家地理》杂志后发现:
杂志以声称的非营利性和科学权威维护其中产阶级价值观,包括培养见多识广的世界公民,尤其是在新时代里促进美国人的全球责任感。然而,实际上,《国家地理》杂志并非一个关于第三世界以及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思想与观念的自由平等交换平台。它只是一本闪耀着光泽的、对特定主题与形象进行高度程式化表述的杂志。[26]
虽然来自两位人类学家的批评相当尖锐,但翻开这本杂志,我们却发现一直以来,它与人类学的关联既微妙又明显。就在1988年一百周年特刊上,该杂志刊登了一组漫画,搜集不同时期其他刊物对该杂志的“嘲讽”。一幅选自1950年《时尚先生》(Esourire Magazine)的漫画,描述在太平洋一个岛上的土著社区里,几个妇女腰系草裙,还有一位穿着时尚连衣裙,她们神色慌张地向茅屋外张望(图2)。漫画标题为“《国家地理》记者来了!”漫画的下方有一句话:“快,快!快换上你的草裙,《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来了!”[27]1984年,另一位漫画家加里·拉森创作了类似的作品(图3),只不过土著们慌忙藏起来的是电视机、留声机等现代生活用品,漫画下方的话为:“人类学家!人类学家来了!”[28]显然,两幅漫画都旨在调侃外来者过度猎奇甚至制造“原始”他者,以及“他者”在旅游业、人类学影响下的自我“原始化”行为。

图2 “《国家地理》记者来了!”《时尚先生》,1950年

图3 “人类学家来了!”加里·拉森《寻找远方》漫画集,1984年
实际上,这份兼具科普与大众传媒特色的杂志,经由“地理”,与人类学和民族志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笔者拟将《国家地理》定位为一种“多型文本”,地理科学、旅行游记、文学作品与民族志混杂相生嵌合,共同组成意义深远的“人类学写作”。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人类学与地理学紧密相连,难分彼此。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而地理学是“对地球的描述”。在德国,民族志这一术语“最初是被描述成地理学的类似物”。[29]人类学也是多学科交叉结合的果实,英国人类学家阿兰·巴纳德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古希腊哲学家和旅行家、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旅行家以及后来的欧洲哲学家、法理学家及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们,似乎都可以算作人类学家的先驱。[30]以希罗多德为例,他的《历史》一书来自旅行见闻,他又被尊称为“人类学之父”。[31]
在学科边界模糊融通的时期,“人类学家”的田野知识大多来自一系列多点、多样的旅行。但自“科学的人类学”建立以来,“田野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标准化被特别强调,正如弗雷泽描述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他成年累月地待在土著人中间,像土著人一样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用他们的语言交谈……”[32]时过境迁,伴随交通和通信技术快速发展,时空压缩与旅行模式发生改变,流动社会形成,学者们对人类学中“田野”的界限与基础又有了新的反思。古塔与弗格森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标准化田野“原型”带来了一些重要结果,其中之一,“是某类知识的霸权及其对其他类型知识的排除”。[33]“其他类型知识”,包括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旅行作家的异域知识书写,就来自多点、多样的旅行,而这正好是《国家地理》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知识来源。在古塔与弗格森编著的《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一书中,詹姆斯·克里弗德讨论了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的关系,他认为,从20世纪之初开始,人类学学科的、专业的实体已发生变化,与文学或旅行实践相结合。田野工作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的居住和旅游的混合实践形式。田野发生在更广阔的和偶然的旅行过程中,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可控制的研究地点内。[34]在《路线:20世纪晚期的旅游与迁移》中,詹姆斯·克里弗德又指出,20世纪的民族志,是一种在现代旅游中不断发展着的实践活动,因此在构造和表述“文化”时,已对以往那种特定的“地点化”的策略越来越警惕。[35]
可以说,当人类学家认为田野调查可能越来越成为“一种研究工具而不是构成专业研究的必要条件”时,[36]《国家地理》却越来越重视书写者的人类学取向与资格。《国家地理》以“增进与传播地理知识”为己任,作为一份人文旅游刊物,此任务主要通过旅行者来实现。与一般浮光掠影式的游客不同,《国家地理》极其强调作者与摄影师的田野调查人资格,包括时间长短与主位意识。比如在2008年5月的“中国:巨龙之内”特刊中,[37]杂志对每篇文章的作者与摄影师的介绍都强调他们与中国的长期关系,如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出版了《寻路中国》;弗里茨·霍夫曼住在上海,他从1995年起就一直记录中国的成长与变化;谭恩美常回中国探亲,她将在下一部小说中着重描写贵州地扪;林恩·约翰逊最喜欢的拍摄任务就是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特定地点”可以转化为旅行“不定线路”的今天,由于《国家地理》书写者本身的人类学方法取向,故笔者将《国家地理》的旅行文本视为一种民族志。如何从民族志的眼光解读《国家地理》里的旅行文本呢?克利福德·格尔兹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指出,审视民族志的一个好起点在于场景设定、任务描述、自我呈现的开头几页。[38]我们以华裔美籍作家谭恩美在《国家地理》上的一篇文章《时光边缘的村落》为例,更好地理解旅行民族志的特征。[39]
文章一开始,作者谭恩美便以第一人称出场,[40]“我”带领读者“见证”所有细节——中国贵州省一个侗寨里的土路、山谷、农田、小姑娘、老奶奶、棺材,情节丰富而描述确定,是“我在场”的有力证据。这正是克利福德·格尔兹称为民族志的情境性特征:作者“署名”或“在场”。这一特征的实质,是使读者信服其所说的,是证明他们实际渗透进另一种形式的生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真正“到过那里”(been there)。[41]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作者书写的村落处于“时光边缘”,对于“时光中心”的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异质性空间。作者在这个异质性空间内的参与观察、解释方式和文本表述,相应建立起“文本”与“本文”(context)中的各种关系,包括“我-他”“主体-客体”“知识-权力”等。
需要指出的是,《时光边缘的村落》这一单个文本只是《国家地理》整体叙事里的一个类别、一种类型。正如克利福德·格尔兹对《忧郁的热带》一书的定位,他认为该书既是游记、民族志报告、哲学文本,又是改良主义宣传册和文学作品,该书形式上兼容并包,而所有文本类型组合、转喻,交织产生出的是一个共同的“探索故事”。[42]借用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转喻性邻接文本”之说,我们可以把谭恩美的这个小文本嵌合进更大的框架——一百多年的《国家地理》之中,让我们沿着纸上之路,看看传教士丁韪良,植物学家洛克和威尔逊,动物学家乔治·夏勒,人类学家拉铁摩尔,探险家黄效文,作家彼得·海斯勒……这些人书写与建构了一个怎样的人类“探索故事”。
[1] Rollin T.Chamberlin,“Populous and Beautiful Szechu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Dec.1911.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名称经历数次变化,最开始为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后改为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最后定为National Geographic并沿用至今。本书统一采用《国家地理》译名,在此后的注释中,一律缩写为NGM。
[2] 〔意〕翁贝尔托·埃科:《他们寻找独角兽》,载乐黛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12页。
[3] Sam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1993),pp.22-49.
[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161页。
[5]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231~238页。
[6]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8、255页。
[7] 〔英〕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李自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35页。
[8] James Clifford,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Literature,and Art (Cambridge,Mas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55-276.
[9] 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10] 〔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前言第1~2页。
[1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44~54页。
[12]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
[13] 曹顺庆、王敬民:《文明冲突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
[14]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2991页。
[15] 关于“西南”的地理范围历史演变及文化含义变迁,重要参考著作有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2007年再版);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参见王璐《文学与人类学之间:20世纪上半叶西南民族志表述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6]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总序”第9页。
[17] C.D.B.Bryan,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Abradale Press,2001).
[18] Nicholas Clifford,“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1880-1949(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19] Ernest H.Wilson,“The Kingdom of Flowers”,NGM,Nov.1911.
[20] 〔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明、明毅译,中华书局,2006。
[21] 〔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
[22]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3] 〔美〕路易莎:《少数的法则》,校真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24] 参见学会官方网站: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about/,Accessed on Jul.17,2020。
[25] William Howard Taft,“Some Impressions of 150,000 Miles of Travel”,NGM,May 1930.塔夫脱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会长吉尔伯特·格罗夫纳的表兄,也是该学会的董事局成员。
[26] Catherine A.Lutz and Jane L.Collins,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5.
[27] Roy Blount Jr.,“Spoofing the Geographic”,NGM,Oct.1988.
[28] Gary Larson,In Search of the Far Side (Andrews McMeel Publishing,1984).
[29]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84页。
[30] 〔英〕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第16页。
[31] 〔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四版),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第16页。
[32] 〔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序”第1页。
[33] 〔美〕古塔、〔美〕弗格森编著《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16页。
[34] 〔美〕詹姆斯·克里弗德:《广泛的实践: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载〔美〕古塔、〔美〕弗格森编著《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2005,第190~204页。
[35] James Clifford,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9.
[36] 〔美〕古塔、〔美〕弗格森编著《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16页。
[37] Special Issue,“China:inside the Dragon”,NGM,May 2008.这期中国特刊刊发了六篇文章:Peter Hessler,photographed by Fritz Hoffman,“China:inside the Dragon”;Amy Tan,photographed by Lynn Johnson,“Village on the Edge of Time”;Ted C.Fishman,photographed by Greg Griard,“The New Greal Walls”;Brook Lamer,photographed by Greg Griard,“Bitter Waters”;Peter Hessler,photographed by Fritz Hoffmann,“The Road Ahead”。
[38]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14页。
[39] Amy Tan,photographed by Lynn Johnson,“Village on the Edge of Time”,NGM,May 2008.此处译文参见《当代贵州》2008年第9期上的同名文章。
[40] 《国家地理》杂志从1906年3月的《摩洛哥》一文开始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文体便脱离“单调乏味”的专业术语和科学体。见Ion Perdicaris,“Moroco,the Land of the Extreme West and the Story of my Captivity”,NGM,Mar. 1906。
[41]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6页。
[42]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