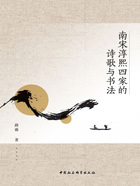
引言
文学与艺术共同具有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所精心设计出来的作品四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包括“人和人的行为、观念、情感、物质和事件,以及超感觉的实体”)和读者。[1]这种划分在分析个别单一的、具体的作品时可能会显得略为简单,但为我们提供了在诗歌与书法两种艺术之间进行综合研究的视角和线索。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书法作为线条的艺术,都打上了创作主体的烙印,展现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追求,共同体现创作者的文化积淀、生存境遇、人生态度、精神境界等。因而,南宋“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的创作成就、艺术风格亦均与作者的学识、涵养、性格、追求等密切相关,且随着时代变迁、文化更迭,二者的关系越来越丰富与深入,并呈现出与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文艺审美思潮紧密相关的特点。
一 南宋“淳熙四家”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2]当文人的言志之诗受到社会背景、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和限制,心中之志不能全部“发言为诗”时,那些未能完全表露的思想及情感就会通过其他渠道表达出来,书法便是其中之一。如唐代张怀瓘《书断》所言:“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3]书法相较于诗歌而言,表意较为曲折、朦胧、隐晦,可以很好地言诗之不尽,补诗之不足,完整地呈现诗人作诗时的未尽之情。两宋时期,文人经常集学者、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除时代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之外,他们的综合成就很好地体现了文学与艺术的相通性。因而,在对宋代文学进行研究时,可以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这些艺术的实践或鉴赏成果来对文学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文学研究被孤立或割裂。[4]北宋时期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书法史上的“宋四家”[5],他们的书法创作堪称宋代不可逾越的高峰。同时,他们在文学方面亦有成就,尤其是苏轼和黄庭坚在诗歌领域具有突出影响,他们使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基本定型,推动宋诗在诗歌史上与唐诗比肩而立,可谓艺舟双楫。南宋时期,以“淳熙四家”为代表人物的文学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
清代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指出:
淳熙书家,就所见者而论,自当以范(成大)、陆(游)与朱子为大宗。皆有宗法,有变化,可以继往开来者。樗寮(张即之)易入,可称“南宋四家”。朱子以道学掩,范、陆以诗名掩,而樗寮以笔法授受有传,名乃独著。朱、范、陆皆出景度(杨凝式),而朱所得独多。[6]
沈曾植本人精通于史学、诗歌与书法,对两宋书法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因而他综合近七百年人们对南宋书法的整体看法,对南宋一代的书法家作出的评价可谓非常严谨、公允。他提出的书法史上“南宋四家”的概念,即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即之,对于书法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在沈曾植论述的基础上,以张孝祥代替张即之,将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四人合称书法史上的“中兴四大家”。[7]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为了使书法史上的“中兴四大家”与文学史上的“中兴四大家”[8]有所区别,将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称为南宋“淳熙四家”。[9]本书选择采用“淳熙四家”之说。淳熙四家不仅代表了南宋前中期书法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文学领域尤其是诗歌方面的造诣和成就亦不可忽视,诗歌与书法彼此衬托,交映生辉,在诗歌与书法的创作、思想及风格方面都具有诸多内在关联。而且南宋前中期的诗歌与书法与宋室南渡初期相比均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思潮及文人、书法家的生平经历、思想观念有关联,在淳熙四家的文学思想和书法理论及相关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有人曾以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陆游等人开始步入仕途为标志,分析当时诗坛的诗人年龄状况:
表0-1 绍兴二十四年(1154)南宋主要诗人年龄一览[10]

续表

从表0-1对绍兴二十四年(1154)“淳熙四家”及诸位诗人的年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宋诗人群体中,陈与义、吕本中、叶梦得、刘子翚等南渡后的江西诗派骨干力量已乘鹤西去,张元幹、朱敦儒、李清照、王庭珪、曾几等诗坛前辈多已到花甲或古稀之年,而陈亮、辛弃疾等后进尚属少年时期,刘过、姜夔、叶适等后辈还在幼儿期,诗坛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中兴四大诗人”及朱熹、张孝祥就是承接前后两代诗人的关键人物,处于重要地位。因而可以说,“淳熙四家”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四人作为在南宋初期成长起来的一批文人,无论是在年龄、时代使命方面还是在对江西诗派的追随及之后的突破上,都是南宋诗坛转变历程中的枢纽人物,他们对诗学的继承和创新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赵构曾感慨:“书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直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11]赵构看到了南宋书法已开始走向衰落的客观现实,指出以书法名家者唯吴、徐二人。吴说善小楷、草书、行书,取法魏晋钟、王和唐人孙过庭而习得书法门径,较为崇尚阴柔之美。他的创新主要在于褒贬不一的游丝书,即一种“一笔书”大草的翰墨游戏,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充其量是南宋初期寂寥书坛中略具“创新”的书法花絮而已,对书学发展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徐兢善大、小二篆,其真行书取法唐人,遒丽飘逸,晚年好草书,追宗怀素书风。南宋初期书坛留名的还有“中兴四将”刘光世(1089—1142)、韩世忠(1090—1151)、岳飞(1104—1142)、刘锜(1098—1162)的书法,其中以岳飞后世声名和书法影响最大。目前传世的作品基本为后世仿造,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未有其墨迹真笔传世,然不影响其书法的历史价值。据岳飞之孙岳珂等人的记载,岳飞“夙景仰苏氏笔法,纵逸大概,祖其遗意”[12]。而且就当前传世临摹作品来看,其书法出自学苏轼一路是可以肯定的。可以看出,淳熙四家之前的书法基本以继承前代书风为主,自创新意的程度已大不如北宋时期。这种书学状况的形成,与当时漂泊动荡的朝廷政治背景有关。国家不幸,书家自然缺少潜心钻研书法、推陈出新的条件和心态,故而书法基本是在前朝风格的笼罩下缓慢前行。而且,南渡的混乱时局造成诸多书法典籍散佚,南宋书家学习借鉴的前代经典碑帖数量有限,是南宋初期书坛萎靡的又一原因。从书法审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书法的创新求变意识在前朝风格笼罩下有所倒退,这就给淳熙四家登上书法舞台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变的背景,为他们继承以及变革既有的文学艺术风格确立了前提。
二 诗歌与书法的历时性关系
现存最早的诗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民间普通劳动者的捕猎之歌。《诗经》三百余首诗歌中富有民间特色的国风便有在劳动人民中流传的过程,经“献诗”“采诗”等方式为居庙堂之高者所认识和接受。无论是口耳相传的民歌还是士大夫创作的文人诗歌,均承载着一定的思想感情。中国书法史自甲骨文时期开始,当时书法最重要的功能还是记录。书匠、书吏所记录的内容多是与统治者有关的史实、政令、言论等。诗歌在具有奏唱、外交、教化及教育等社会性的功用之外,在民间及中下层文人中依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如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楚辞、《小雅》中的部分中下层官吏所作的诗歌等,而书法更多的是承担统治者及上层社会的文字记录功能。
秦王朝一统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规范政策,使各体文字和书写方式统一到秦小篆上来,并将其推广到全国,李斯和他所作的《峄山石刻》在文学史和书法史上均得以留名。但秦代诗歌与书法发展不平衡,诗歌鲜有名家名作。此期诗歌由口头语言转向书面形式表达出来,这是诗歌与书法在实用性层面的重要联系,即书法的意义也附着于文字,与诗歌非自觉地结合,诗人与书法家按照各自领域的规律进行创作,似二水分流,相互独立,尚未形成交汇。
汉代的文学与书法分别进入自觉时期。因“文学自觉”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且关于“自觉”一词,也因评价标准、研究视角差异而有不同阐释。[13]因此,与其追溯文学自觉的源头或起点,不如探讨文学的自觉何时基本实现。两汉时期,文学已基本实现了其独立与自觉。[14]诗歌在汉代获得了极大发展,四言诗成熟,五言诗兴起,将诗歌创作推向更高水平,文学批评开始对文学进行理性思辨。同时,在中国书法史上“书法在汉代已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两汉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15]。汉代重视书法教育,涌现出了一大批书法家,皇家和民间都开始收藏名家的书法作品。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方面的著作也陆续兴起。东汉时草书兴起,草书书写速度快,笔势放纵,气势连绵,能够很好地展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使个性得到自由发挥。文人五言诗也兴于此时,作者在诗歌中思考社会人生、彰显主体意识,诗歌与书法抒情达意的功能在两汉时期得以确立和展现。
“文人有意识地从事书画艺术基本上始于东汉,特别是桓、灵时期,随着人们对草书美的发现和鸿都门学招收书画人才所引发的全社会对书画的趋之若鹜,文人从事书画已蔚成风气。魏晋以后,这种风气越来越浓,从而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兼擅文学和书画的通才型艺术家,形成了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16]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约束力相对松弛,为思想自由留出空间。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动摇,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和艺术解放,文人与艺术家的身份界限逐渐模糊。“汉魏风骨”“魏晋风流”在诗歌和书法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诗歌题材和内容不断扩展,文人喜谈玄学佛理性命之学,体现在诗歌中风格偏向玄妙飘逸。[17]同样,魏晋书法“尚韵”,一方面是时代使然,另一方面也来自老庄哲学、艺术精神的渗透。文人可以在书法的挥洒中入虚探玄,超脱一切形质实在,使书法成为性灵之自由的抒发与表现。[18]此期诗歌和书法都具有家族和集团式特征,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陈都谢氏、吴郡张氏都是诗书皆通的世家大族,魏时诗坛有邺下集团现象。[19]王羲之是文学与书法结合的枢纽人物,他的《兰亭集序》是重要代表作品。东晋后期,以王献之为代表人物的书法继续向着新妍的方向发展,王献之书法“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20]。“媚趣”也是东晋后期书风胜过中期之处。此时的诗歌亦重在抒写创作主体的个性、性情,诗风转向流丽、轻艳,向南朝宫体诗过渡,同书法之“媚趣”具有大致类似的发展方向。南北朝时期诗歌与书法发展的一致性还在于均出现了南北之别。[21]若将北朝古朴厚重的魏碑与铿锵激昂的《木兰诗》、南朝疏放妍妙的行草与清丽婉转的《西洲曲》置于一起,会发现同一地域诗歌与书法的艺术风格、审美取向有很大相似之处,尽管南北迥异,但彼此影响渗透,互相取长补短,诗书风格更加完备。
隋朝基本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和混乱,政权的统一带来了南北诗风、书风的融合。中国沿袭千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隋朝设立,为唐代诗歌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书法上接北朝,下启三唐,各体书风别开生面。唐代诗歌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体制齐备、流派众多,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成熟。《全唐诗》序曰:“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22]唐初诗歌注重“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研揣声音,浮切不差”,创建了新的诗律,在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点与唐代书法之崇尚法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代对流外吏胥的叙用纳入“工书”一项[23],欧阳询、虞世南等名家遵循“楷书遒美”的规矩,写字中规中矩,法度森严。中唐后国力渐衰,社会风俗、名物制度等的强化需要更多法度和规矩,崇尚法度的书风日渐形成。此外,唐人草书也是一大特色,以“张颠素狂”为代表的行、草书大家及其作品,重视创作主体感情和个性的发挥,与楷书形成共存互补的局面。至此,唐代诗歌与书法重情尚法成为主要特色。
有宋一代,文学创作反对模拟,强调创新。如梅尧臣提出“意语新工,得前人所未道”[24],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提出要善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25]。宋代士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关注时事,长于思辨,各体文学都染上了较为普遍的理性思辨色彩,感情抒发偏于婉转沉潜,文体间互相借鉴,拓展新境。两宋书法改变唐人书法重视法度的成规,提倡尚意书风。[26]他们通过书法作品展现个人学问、性格、情趣、修养、品性及胸襟抱负等精神内涵,彰显书法抒情达意的功能。“宋四家”尤其是苏、黃、米三家以意造奇,主张尚意书风,以更适合于抒发意趣和情感的行草见长。诗歌和书法作品的学问气、书卷气增加,更加重主观、重个性、重神韵。在宋室南渡后,南宋书法学习“宋四家”成为一种主流。[27]淳熙四家书法中已现古意与尚法潜流,其他重要的书法家如吴说、王升、蒋灿、吴琚、姜夔、张即之及宋末元初的赵孟頫等人也都以继承传统而著称,不以书法名世的沈括、董逌也都注重法度,在理论上予以阐扬,形成宋末元初书坛复古主义的前驱,为元代书法理论重拾“法度”而远离北宋尚意书风奠定了基础。
元灭南宋后,忽必烈接受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诏修孔庙,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官方哲学,加强政治与思想统治。元代诗学主要继承南宋理论,也吸收了金代文学特色。如王若虚反对过分追求形式上的人工雕琢,元好问主张自然天成,反对闭门觅句,对后代诗学理论有很大影响。元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成果并不突出,小说戏曲则开始萌芽。书法方面,“自元代起,中国古典书法美学便显露出终结的迹象”[28]。元代书坛的新兴风气之一就是对“法”的重新尊崇与坚守,元代的书家、书论鲜有不言“法”者。虞集《道园学古录》“君子作事,必有法焉”[29],品评历代书家作品都以“法度”为准绳,视其对“法度”的继承与破坏而做出评价。元人郑杓在《衍极》中指出,“五代而宋,奔驰崩溃,靡所底止。”[30]抨击宋代尚意书风末流,提出托古改制,以正时风,树起越唐入晋的复古大旗。明代的前后七子也以复古之法来挽救明代文学的凋敝衰微,并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一以退为进的诗学策略与书法规律有意无意间合拍。有学者指出:“在元人统治下,赵氏(孟頫)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31]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还是应该把其复古之意放在整个纵向的诗歌与书法发展历史中看,无论是诗学还是书学的复古尚法,元明文人师古人之迹,取古人之貌,师古人之心,取古人之神,扬古人之法,妙合化机,正是自南宋而来复古尚法之风的延续与升华,是艺术发展的必然流向。
明代自嘉靖后期开始,文学艺术上又出现了反复古的新思潮,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限模糊,诗歌、书法也受到通俗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诗歌方面,公安“三袁”提出“性灵说”,提出作诗应当直抒心胸,抒写性灵,流露自然天性。竟陵派以“幽深孤峭”矫其后学之俚俗,为反对复古模拟的“心之元声”“正变”说等理论奠定了基础。此期亦是书学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反帖学呼声渐高,祝枝山、徐渭等人对书法之“法”提出质疑与抨击,为超越法度提供了契机。清代,诗歌在宗唐与宗宋的主张中发展,碑学的兴起也将书法的关注层面从阳春白雪转向世俗与民间,是对书法艺术情境、范围的最大开拓与变革。诗歌书法复古与创新、尚法与尚意一定时间后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反映出的是文人艺术家们求新求变的意识和努力。
诗歌与书法自先秦及秦代时的二水分流、双峰并峙到两汉时期实现独立与自觉,魏晋南北朝时交融会通,唐宋时期法度与意趣交叠,再到元明清时期诗歌与书法重归法度又超越法度,向现代转型迈进,描绘出一幅诗歌与书法在文化历史长河中相互交叉又独立发展的关系图。就诗歌与书法的历时性关系而言,二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变化轨迹,时而交汇,时而分流,这也是在学科交叉点上进行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综合研究的另一缘起。[32]
三 南宋淳熙四家的诗歌与书法
在对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即跨艺术比较最常见的一种方法性的错误,即不能意识到某种特点在一种艺术中确实存在,而在另一种艺术中只是间接和引申地存在。因此在研究诗歌与书法这两种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时,选择所要比较的某些特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特点必须切切实实地存在于被比较的作品之中,而不能牵强附会,一一对应,按图索骥。[33]
南宋偏安一隅,国力不如北宋,整体来看南宋文人及其各类创作基本上被一种脆弱伤感的氛围所笼罩。尽管南宋文化艺术中也有豪放、纵意的情怀,表现形式各有特点,但南宋国势的衰微,毕竟使南宋诗歌、书法没有出现北宋那样百家争鸣、名家辈出的盛况,也缺乏唐代文化包容、自信的宏大气象。南宋前中期,发生在诗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就是通过陆游、范成大等人的改进创新,宋诗走出了江西末流艰涩模仿的瓶颈期,诗歌题材扩大,诗歌意境提升,出现诗歌新变的良好契机。
在书学领域,南宋初期,高宗君臣继承了“宋四家”的尚意书风并进行大力推广,使宋四家与颜真卿一起成为当时普遍的书法取法对象。到了南宋末期,名满天下的“南宋四家”之一张即之的写经书法中,尚意风格渐渐消亡,开始遵循法度,对元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复古”书风产生直接影响。“隋唐五代书法尚‘法’求工,北宋书法转而尚意重情,彰显学问气、书卷气,表现自我个性,形成新的审美风格。南宋书法延续了北宋书法‘尚意’的书风,但也暗藏‘尚法’的潜流。”[34]书法从唐代的尚法之风发展到宋代尚意流行,是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变革。宋末元初之际,书风又出现向“尚法”的回归,这一契机中所包含的书法观念和文化思潮都是非常关键的。南宋前中期的书法,正是南宋书风从初期“尚意”的时代风格向宋末元初追求复古“尚法”风格转变的重要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而淳熙四家在诗风与书风几乎同步的嬗变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本书尝试换一种角度,不再单纯研究陆游、范成大、朱熹及张孝祥个体的诗歌或书法艺术,或局限于一个朝代之内将南宋的诗歌、书法与北宋进行单向比较,而是采取更加宽广的视角,将淳熙四家这一群体置于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的长廊中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他们四人所代表的南宋前中期诗歌与书法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南宋诗风与书风、诗书理论的交替嬗变及其影响等方面,由此淳熙四家的诗歌与书法的重要程度、历史意义才会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本书拟通过梳理南宋淳熙四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分析相关文学艺术作品和诗论、书论中诗歌与书法的题材、源流、形式、风格、审美、思想交融会通或互有反差的内容,对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的艺术成就、文艺思想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对其在当代及后世的影响、地位作进一步的梳理审视,研究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在传播、接受过程中时人及后世不同角度的评价和论述,研究淳熙四家作为诗歌与书法的创作主体复杂的内在精神世界,进一步探究其艺术情感和审美意蕴。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综论,下编为分论。
上编内容共有四章。
第一章论述淳熙四家所处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首先讨论“中兴之治”及淳熙四家的爱国情怀,这是他们诗歌及书法的共同背景。然后探讨淳熙四家诗歌和书法与当时文化思潮的关系,其中帝王倡导对文化风气有推动或导向作用,再对这段时期内诗坛与书坛的基本特征进行综合论述。
第二章论述淳熙四家诗歌书法的继承和创新。淳熙四家的诗歌与书法中的继承对象、学习路径及各自所作创新有重要关联。淳熙四家出入江西诗派、临摹北宋四家是学诗、学书的共同经历。他们由师法本朝名家转而追宗古人,对汉魏两晋古诗及唐诗情有独钟。在学颜真卿书法时认识到法度的重要性,同时学唐代及唐前名家。淳熙四家在借鉴的基础上融入创作主体独有的思想情感,诗书创作推陈出新,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
第三章论述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相关理论。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理论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如淳熙四家对诗歌与书法法度观及道德观的认识,探讨“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说等经典批评方法在南宋的演进;由于人生阅历、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的差异,淳熙四家对于诗歌和书法地位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内容正是代表了南宋前中期诗歌与书法思想理论的时代风貌。
第四章论述淳熙四家自书己诗作品的风格及内涵。本章选取淳熙四家具有代表性的自书己诗作品进行分析,此类书法作品与诗歌内容的风格更加气脉互通、相因相成。与此同时,个别诗歌与书法风格不相协调的作品如陆游《纸阁帖》的成因,亦非常耐人寻味。在此基础上探讨淳熙四家自书己诗作品的创作心理及文化内涵。
下编内容共有四章。
第五章是陆游的诗歌与书法。陆游有大量论书诗,以诗歌的形式将自己书法创作的动机、感悟、心情记录下来,从中可见陆游作书时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酒在陆游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书法创作中都不可或缺,他的诗歌、书法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歌与书法之外的功夫都非常重要,共同促进他的诗书名垂千古,很多作品表现出刚柔并济的艺术风格。
第六章是范成大的诗歌与书法。范成大将行藏出处及从政、为文、游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比较恰当,仕途较陆游等诗人较为顺利,文学、书法贯穿一生,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生活的多面性。他的诗歌与书法风格尚意与典雅兼备,诗歌创作较为客观、理性、严谨,书法显现出尚意书风向复古书风演变的迹象,而且他的诗书思想、理论中也有不少对传统古意的崇尚与实践。
第七章是朱熹的诗歌与书法。朱熹的理学思想对诗歌与书法创作有很大影响,他认为“文道并重”,也时常流露出对诗歌的矛盾心理。他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提倡诗风平和中正才是上品。朱熹亦将理学思想贯彻于他的书法创作和书学理论中,正心持敬,道为书载,将尊崇个性、神韵、趣味的尚意书风向尚理、尚法的方向转移,对南宋末期书风转向尚法复古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八章是张孝祥的诗歌与书法。理禅融会的思想是张孝祥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他诗词俱佳,词的流传更广一些,是豪放词从苏轼到辛弃疾词风转变过程中的过渡人物,他的诗歌在当时及后世获得极高赞誉。书法也在承前贤、启后学方面发挥连接过渡作用。诗歌与书法的风格基本可以归入“清旷”与“豪雄”两大类别,诗书刚劲有力,体现出铮铮“骨”力。
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研究的未尽之意进行补充说明。
本书突破既有南宋诗歌与书法地位影响论的局限,转而关注文人个体生命、身心统一,研究淳熙四家在诗歌与书法中体现出来的个性、学养、胸襟、抱负等。北宋书法领域尚意书风盛行,发展至宋末元初转而变为复古尚法,南宋是重要的过渡阶段;江西派诗歌在南宋逐渐显现出诸多弊病,淳熙四家所处的时期即南宋中兴时期是诗风转变的重要环节。淳熙四家是南宋诗风与书风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因此,本书结合南宋文化、理学的发展,对淳熙四家的诗歌与书法进行综合研究,希冀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将书法史上的淳熙四家概念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将淳熙四家的诗歌与书法成就结合起来,视其为一个文化群体进行研究。二是在南宋中兴时期,诗歌与书法的发展出现一些新的转变,对南宋后期的诗风与书风产生影响,而淳熙四家在诗歌与书法风格嬗变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并结合此时期政治、文化、理学等背景探讨诗书发生变化的潜在原因。三是将淳熙四家诗歌与书法纳入文化的视野之内,突破南宋诗书地位或影响的局限,关注南宋前中期文人通过诗书二艺所表达出来的性情气质、身心统一,也是本书独辟蹊径的立足点之一。
[1]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页。
[3] (唐)张怀瓘:《书断》,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409页。
[4] 邓乔彬、昌庆志:《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第26—28页。
[5] “宋四家”之苏、黄、米、蔡并称,最早见于宋高宗《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蔡,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6] 沈曾植著,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7]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8] “中兴四大家”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关于其具体所指,杨万里在《千岩摘稿序》中说:“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序》引尤袤的话说:“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乎?痛快有如杨廷秀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杼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方回总结中兴诗人的诗歌成就及前人的总体看法,将“中兴四大家”确定为陆、杨、范、尤四人:“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在其《瀛奎律髓》中也说:“乾、淳间,诗巨擘称尤、杨、范、陆。”后世皆沿此说,且在很多情况下“中兴四大诗人”成为南宋中兴诗坛的代表诗人群体。
[9] 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10] 孙延辉:《张孝祥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9年,第46页。
[11] (宋)赵构:《翰墨志》,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369页。
[12]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13] 关于文学何时进入独立与自觉时期,学界先后有魏晋说、汉代说、先秦说等几种观点,现简要罗列如下:自1927年7月,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最先提出“文学的自觉”概念(《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自20世纪80年代起,“文学自觉魏晋说”遭遇质疑和挑战,龚克昌首先提出,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是“文学自觉西汉说”的起点(龚克昌《论汉赋》,《文史哲》,1981年第1期,第37—46页)。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论述(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2003年,赵逵夫《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一文中有“文学自觉于先秦”的提法[赵逵夫《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7页]。以此为滥觞的“文学自觉先秦说”在近年来得到多方认可与探讨。
[14] 汉代把文人分为“文学之士”和“文章之士”,“文章”的内涵和范围与魏晋以后一致,“文章”观念的确立是文学独立的重要标志;诗赋已成为独立的文学大类,从学术文化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以写作文章为主的专业文人队伍,各种文学体裁在汉代形成并逐渐定型。见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15] 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16] 张克锋:《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画论的会通》,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第15页。
[17] 山水诗、咏物诗、田园诗、宫体诗、游仙诗等题材更迭出现,异彩纷呈;战乱频仍,生命脆弱,个人难以主宰命运,建功立业之路曲折,这些都触动着文人敏感的心灵,关于生命苦短、人生易老、生离死别、壮志难酬、及时行乐的慨叹不时出现在诗歌中。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页。
[18] 此期诗歌与书法在创作主体、审美观念及创作方法上,都前所未有的趋于交会。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这一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创作供观赏的书法作品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文人已将“写字”看作一种脱离实用的审美活动,另一方面表明文学艺术对书法艺术具有很强的影响和渗透力。见张克锋《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书法与文学的交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6页。
[19] “曹魏书法随着时代变化确实演进了一步,即使书法是趋应新文风之后而形成新风气,也称得上是‘洛下新风’的重要一翼。”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20]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
[21] 清代阮元《南北书派论》论南北朝书学:“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三○五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2] (清)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23]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2页。
[24]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25]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七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10页。
[26] 尚意书风之“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表现哲理,二是重视表现学识,三是强调表现人品性情,四是注意表现意趣。”见陈训明《宋书尚意浅论》,《书法研究》1984年第4期,第31页。
[27] “以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等为代表的一时名流,学‘宋四家’而又不为所囿,各自变体而有成就。”见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28] 萧元:《书法美学史》,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29] (元)虞集:《论书》,《道元学古录》卷四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元)郑杓:《衍极》卷一《至朴篇》,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408页。
[31]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32] 路薇:《中国诗歌与书法的历时性关系研究》,《学术论坛》2016年第3期,第135—139页。
[33] 孙敬尧:《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34] 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