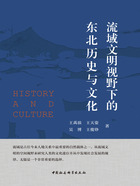
绪论 东北流域文明的研究内涵、历史书写与学术价值
一 流域文明——东北史研究的新视野
近百年以来,众多的考古发现使中华文明“多源一体,辩证发展”的理论观点渐成学术界的共识。从宏观意义上讲,史前的辽河、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等流域的东北历史与文化与黄河、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历史上的东北古代民族在中华早期文明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商周至秦汉,活跃于东北地区的东胡系统、秽貊系统、肃慎系统分别与华夏族系展开了长期的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自此之后,匈奴、东胡、柔然、突厥、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先后或称霸北方,或入主中原并建国称帝。北方民族逐鹿中原、数次横扫欧亚大陆,改变了世界格局,造成了内陆亚洲及东亚区域和中国历史上多次南北朝大融合,并奠定了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及语言通译的基础。这种趋势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满洲人由东北入关,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并最后终结了中华大地上的华夷互变的进程,使长江、黄河、珠江、雅鲁藏布江、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辽河、塔里木河、伊犁河、澜沧江等不同的流域文明归为一统。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正是由东北地区古代民族不断地入主中原而完成的一项伟大的“整合工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问鼎中原,纵横于欧亚大陆的北方民族,几乎都出自中国的东北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犹如一座充满了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历史大舞台,具有巨大差异的不同文化传统在对抗与创新、定居与迁徙、改造与包容、吸收与排斥中得到了进步、再生、继承和发展,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东亚社会创造了连续不断的历史辉煌。
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东北地区辉煌厚重的历史文明和灿烂的民族文化,逐渐改写了东北区域史和人们脑海中关于东北边疆的陈旧观念。20世纪8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就在所谓的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的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数百座汉魏时期的城堡和大型的拜天礼地的祭坛,形制复杂的凤林古城和气势恢宏的炮台山七星祭坛证实了早在汉魏时期,三江平原就已迈入了早期国家的大门,开创了繁荣的城邦文明。学术界认定这是一处被人遗忘了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但至今学术界对其文化内涵和民族源流尚无值得信服而完整的解释。西辽河流域的辽西地区褐色黏土中,层层叠压在一起的距今8000—4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具有东北亚地域早期文明礼制起源意义的红山文化,大、小凌河及老哈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与上层文化之间的来龙去脉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石城建筑,乌裕尔河流域发现的大批极为特殊的石耜与精美绝伦的玉器,遍布东北大地的黑曜石石器的来历,内蒙古高原呼伦贝尔草原地带的哈克文化的细石器与早期的农业文明元素,黑龙江流域上游、中游地区沿岸发现的众多的城堡、下游地区发现的具有中亚和西亚文明意味的人面红衣彩塑陶,以及通化地区发现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障塞、长城,还有在东北地区发现的一千四百余座各时代的古城、都市、山城,辽东半岛上神秘的积石冢、大石棚文化,鸭绿江流域庞大的数以千计的高句丽时期金字塔式的古墓群等,都构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神秘和未知的历史世界。
近年东北地区考古领域亦取得了重大进展,如饶河小南山遗址、葫芦岛东大杖子战国古墓群等。在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小南山遗址中,出土了距今9000年的精美玉器,这些玉器显示出小南山作为东北亚极东滨海地区早期文明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其与后来的辽西红山文化关系密切。小南山早期遗存陶器中的梳齿纹和器物口沿与上部的饰纹风格、双面尖状石器的发现则表明,小南山文化介乎于俄罗斯远东奥西波夫卡文化与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孔东文化)[1]之间,填补了两大文化类型之间的谱系空白,并代表了一支以往未被识别出的新考古学文化,同时亦是黑龙江下游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因素在我国的首次发现。凡此种种,皆反映了乌苏里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具备发达的玉器文明,并深刻影响和辐射了东北亚早期文化格局的演进。除此之外,2011年11月,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大凌河上游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村发现了的古墓群,其中发掘了一座大型战国中晚期的贵族大墓,无论是从墓地的规模还是出土的精美的漆器、仿青铜器彩绘陶器、嵌金青铜短剑、带钩等文物,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概念——“春秋战国考古不出关”的旧说。尤其是墓葬中殉牲的五种牲畜——五头牛、两匹马加上猪、狗、羊的头骨达70余件的祭祀规模更让人疑惑。这究竟是何人才能享用如此高规格的墓葬?马、牛、猪、狗、羊五牲俱全的殉牲方式,迄今为止在北方地区从未发现过。这种具有中原华夏文明和东北古代民族文化的双重礼俗的胡汉之风的战国墓地,为我们的东北流域史研究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根据新闻报道可知,墓中还出土了嵌金青铜短剑、带钩、蟠螭纹盖壶等青铜礼器、红玛瑙环。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彩绘仿青铜陶礼器。虽然整体情况尚不清楚,但可以看出鼎、豆、壶的基本组合也是符合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墓葬规制的。这是一个“两椁一棺”的大型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近年来,在环渤海沿岸及辽河,大、小凌河流域虽然偶有战国时期墓葬的发现,但是其规模都很小。然而,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村这座墓地的发现则是长城以北接近东北地域最大的战国墓葬,值得我们学术界的注意!众所周知,大、小凌河流域一直以来就是东北古代民族与幽燕华夏文明的交汇点或者接合部,这一流域的文化特征具有东北与华夏的双重性格则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东北区域文明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在文明的起源地,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文明的发祥地往往是沿着江、河、湖、海的沿岸分布,并早已被考古工作者们的许多重大发现所证明。中国东北地区特殊的地貌和多变的地势,以及复杂的气候环境,决定了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根脉和走向。事实上,东北的历史与文化也依然沿着东北地区的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而分布着。因此,与其说是东北地区的区域文明,还不如说是“东北流域文明”更加贴切。历史上对东北文化的称谓有“满洲文化”“关东文化”“白山文化”“黑水文化”“辽海文化”“草原文化”“松辽文化”等等,其实这是一种流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复合的概念。如果从流域文明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东北区域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五大流域文明区域的结论:黑龙江流域文明,辽河流域文明,大、小凌河流域文明,鸭绿江流域文明,图们江流域文明。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出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嫩江流域、乌裕尔河流域、乌苏里江流域、浑河流域、太子河流域、浑江流域、布尔哈通河流域等次一级较大支流的流域以及众多小流域文明。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的绥芬河则是一条单独注入日本海的河流,虽然其流量较小、干流里程较短,但其处于北部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与南部图们江流域之间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流域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也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流域文明。虽然它们均属于东北的流域文明,但由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使各自所影响的区域文化呈现出一种缤纷多彩、百花齐放的景象。
建立过勿吉国、渤海国、大金帝国以及清帝国的靺鞨、女真、满洲这一系统的民族便祖祖辈辈都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于黑龙江流域之中,主要是三江平原至牡丹江流域中下游;东胡系统中的乌桓、鲜卑、奚、契丹、蒙古等族的兴起与衰落与西辽河流域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室韦则是黑龙江上游呼伦贝尔地区和嫩江流域的重要古代民族;大、小凌河流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幽燕文化与东北文化及草原游牧文化、海岱文化的交汇点,同时不少学者认为殷商也是发源于此;鸭绿江流域是秽貊族长期繁衍生息的区域,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这里的金字塔式积石墓与精美的壁画代表了这一地区民族留下的灿烂文明;图们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便利等特点,使这里成为古代民族理想的聚居区,历史上的秽貊、沃沮、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洲等民族,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图们江流域所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和繁盛的都市文明,大祚荣初建“靺鞨国”(即后来的渤海国)也是以此为根据地。正是因为东北地区复杂和多样的生态环境,使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文化并非单一类型的民族文化,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多种经济模式结合的复合型的特殊文化形态,所以它是中国历史上充满神秘、充满活力、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上述这五大流域文明,除辽河流域文明和大、小凌河流域文明外,其他三大流域文明均具有跨越国境的特点。流域文明的研究方法能回避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境线限制,在超越时空的前提下采用地理环境的影响,以流域的空间文化实现跨境的覆盖,去了解远逝的真实历史。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东北流域的地理形势,就会清晰地看到,那些江河纵横的水系网络犹如历史文化列车的交通轨道。中国历史上的东北地区是一个更辽阔、更富于变化的舞台,那些沉睡了千年的众多古城,就是东北古代民族的城邦和都市。
中国东北地区的五大流域文明曾经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的北方五大帝国王朝,即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女真人建立的大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大元王朝、满洲人建立的大清王朝。此外,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在这五大流域之间还建立了若干个侯国、属国和方国,例如:朝鲜侯国、貊国、秽国、橐离国、夫余国、勿吉国、豆莫娄国、乌洛侯国、孤竹国、屠何国、三燕政权、高句丽国、渤海国、后金政权等数十个方国、侯国与王国。从上述的五大王朝和众多的方国、属国与王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事实:其一,一千六百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政权,有许多是由繁衍生息在中国东北这五大流域之间的古代民族建立的;其二,中国历史上两次南北朝时期的形成,都是因为东北五大流域古代民族南下,这种民族移动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由华变夷、由夷变华的“华夷互变、胡汉相融”的过程;其三,中华文明在语言文字、文化、艺术、文学、杂剧、小说、宗教、城市文化、石窟艺术、都市文明等方面达到了灿烂辉煌的历史阶段;其四,使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继续扩大和延续,使中国古代东北疆域开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五,商品经济异常繁荣,都市文明迅猛发展,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均出现了都市文明的繁荣局面,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其六,促进并扩大了对外交流,开辟了新的海路和陆路,推动了科技进步与发明、发现及探索;其七,中古时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王朝更替,除了宋、明王朝之外,几乎都是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朝或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政权,这些东北古代民族曾经作为统治民族的地位而影响了东亚乃至欧亚大陆。然而,在传统的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存在认识上的偏见。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东北的流域文明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东北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王朝政权以及属国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今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由于人们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才使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正在渐渐地消除”这句话的分量。只要将百年以来的考古发现摆上案头,进行理性思索,我们便会从固有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千六百年的中国历史,为什么只有东北民族才具有不断问鼎中原的力量?东北民族与中原古族、古国有无亲缘关系?为什么东北民族的氏族制在一个民族勃兴时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东北的五大流域为什么能够孕育出如此强大的民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由于东北民族一次次入主中原,造成了沿着长城从东到西的一个方向上的重大变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长城内侧一系列的社会秩序和各种关系的重新组合。从已经逝去的历史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上分析,当时人们在文化接触之后,长城内外的人们各自所产生的心理负担相当沉重,几经沧桑后的心理平衡过程充满了痛苦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