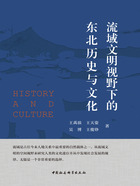
三 流域文明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和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纲要》三部作品共同开创了我国东北通史研究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北地方史研究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再次焕发了勃勃生机。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薛虹、李澍田主编的《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程妮娜主编的《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多部东北通史类著作,以及诸多东北断代史、民族史与东北专题历史研究著作相继问世,有力地助推了我国东北边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但这些学术专著多深受传统史学学术理念的影响,往往侧重从民族、风俗、地方政权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等角度,或以当前的行政区划解读东北某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然而,在历史上,东北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存在并非以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行政区划而分布着,而是沿着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而分布着。同时,流域文明与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区域史、边疆学、跨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以及当代跨国区域合作与交流等均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以全新的流域史和流域文明的视角和研究范式,重新审视和整合东北区域历史与文化,以流域淡化行政界线,以流域打破国界,以流域重新整合区域。如此,以宏观的流域文明视野研究和论证古代文明,特别是边疆地区的跨国历史文化,便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其一,流域文明研究范式对民族学的意义与价值。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生存和繁衍着为数众多的古代民族,事实上,“逐水草而居”不仅是北方草原和西北高山牧场地带的游牧民族生存与生活方式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绝大多数温带与亚热带民族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这一点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南疆盆地表现得尤为突出。上述地区气候干旱、雨水稀少,民族群落往往沿河流及绿洲呈带状或星罗棋布般分布。以今伊犁为中心的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由于其宜人的气候和水草丰美、适宜放牧的高山牧场,这里自古至今都是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大熔炉。塞种、乌孙、大月氏、突厥、回鹘、葛逻禄、喀喇契丹、察合台蒙古、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演绎出绚烂悠久的伊犁河流域文明图景。在蒙古高原上,匈奴、柔然、高车、突厥、蒙古等强盛一时的游牧民族始终围绕着三河源之地即土拉河、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而活动,并以其为根据地实现对外扩张。
流域文明对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史的研究意义尤为凸显。这是因为,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使狩猎采集与渔猎、游牧、农耕等不同生产方式同时存在。纵观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河流的发源地或汇聚地往往是古代民族繁衍的聚居区,而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则构成了东北古代民族迁徙的路线图,并进一步被固定化和行政化为重要的文化走廊和交通孔道。如分布于乌裕尔河和嫩江流域的索离国,其王子沿嫩江流域南下进入松花江流域的今吉林市一带,建立了夫余国。索离人的南下推动了原分布于吉林市地区的秽人南下越过哈达岭和龙岗山脉,进入浑河流域和辽河大平原。夫余国王子邹牟沿着与秽人南下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辽东的浑江流域,并在浑江与富尔江交汇处建立了以纥升骨城(今桓仁五女山城与下古城子)为王都的高句丽政权。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则是沿着浑江河谷进入鸭绿江流域,在狭窄的鸭绿江中游河谷溯江而上抵达今吉林省集安市。肃慎—满洲族系的分布则始终没有离开牡丹江流域,从肃慎王城即今宁安三家子古城的建立到渤海国的建立并定都上京龙泉府,再到女真始祖函普至昭祖石鲁等历代女真祖先,肃慎族系中的各民族长期以牡丹江流域为活动中心。在满洲族源神话中,始祖布库里雍顺乘舟自“布尔湖里”(今长白山天女浴躬池)顺牡丹江而下至“三姓”之地(即今依兰县),并最终定居“俄漠惠之野”的“鄂多里城”(今敦化),可以说,满洲族源神话几乎完全是滔滔牡丹江水孕育的结果。牡丹江流域下游的依兰县一带正是建州女真的发源地。与此同时,由于古代民族的分布与迁徙得益于河流走向,当今国际环境的变迁与新国界线的划分使许多古代民族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致使其族属、地位、民族源流等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流域文明视角对边界的淡化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跨国境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也促使相关国家和地区消除民族主义情绪对历史研究的主观影响,更加客观地看待民族问题。因此,从流域文明的角度全面梳理和解析古代民族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能够更加直观和清晰地看清其发展与迁徙的历史经纬,同时也实现了与各民族“逐水草而居”这一历史事实的有机统一。
其二,流域文明研究范式对区域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由于现实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改变,历史研究被认为过多地片段化和碎片化,微观主义和“各自为战”式的研究理路使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受到了巨大冲击,使人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以区域史的研究视野、理念与方法,对片段化、碎片化的研究材料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全新整合,抛弃传统的国别史和朝代史的研究思路,即开展宏观视野下的微观研究应成为历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流域文明事实上正是区域史研究范式的最新呈现,即以流域为单位,探索和梳理历史经纬的来龙去脉。以流域文明为切入点的区域史研究也打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地方史研究范式。河西走廊的石羊河、金川河、黑水河、疏勒河、党河等流域始终是该地区古今民族文化和城市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并形成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重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因工业化建设而诞生的金昌、嘉峪关等新兴城市也是因其分别处于金川河流域和讨赖河流域的中心地带。以流域文明的视角进行研究,事实上更能立体化地展现河西走廊的历史发展。在新疆地区,具有鲜明欧亚化或内亚化色彩的西域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河流孕育出的绿洲文明,塔里木河及其支流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车尔臣河、阿克苏河、孔雀河等以及吐鲁番盆地的罗布泊成为孕育绿洲文明的摇篮,楼兰、鄯善、高昌、龟兹、于阗、尼雅等繁盛一时的西域城邦无一不是流域文明的馈赠。对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中辽河流域与大、小凌河流域文明的研究,同样能够以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态度,展现相关区域的历史与文化。
其三,流域文明研究范式对边疆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边疆地区是区域史视野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对于涉及多国的跨国边疆史而言,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当今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国境线的走向而转移,而更多地呈现出区域性和边疆性的特征。以中国东北为例,当今中国东北疆域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东亚近代史和东北亚国际环境变迁的产物,作为“东北亚内陆”的东北边疆,周边环绕着蒙古国、俄罗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东北亚三国,在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中,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以及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均具有跨国境的特点,东北边疆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便常常与国家利益、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杂在一起。研究这一边疆地带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回避当代国境线两侧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与关系,如果一味地从当代的政治地缘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一旦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刺激,对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复杂,继而由学术问题转变为牵涉国家利益的政治问题。因此,以流域文明的视角解读边疆史和边疆学,有利于相关诸国学者淡化国界意识,缓和国家和民族的情绪对立,消弭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极端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弱化因疆界划分而产生的对历史的阉割,增强整体史观念,客观理性地开展跨国境的政治史、政权嬗变史、民族发展史、文化交流史、与中原王朝关系史等研究工作,避免历史问题现实化、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和现实政治与民族问题的历史化。
其四,流域文明研究范式对东北边疆跨国区域社会发展与交流合作的意义与价值。以流域文明的视角展开对东北亚跨国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这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对我国与相关周邻国家的跨国区域社会发展与彼此间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流域文明的视野重新整合了跨国区域间联动,促进各国在挖掘历史、进行文化建设方面进行广泛合作,为当前我国与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等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历史参考和制定现实政策的依据。同时,流域文明的研究范式将有助于黑龙江两岸中俄城市,黑龙江流域上游的中俄、中蒙接壤地带,鸭绿江两岸中朝城市以及中、俄、朝三国在大图们江区域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为经贸品牌的打造、文化建设、旅游资源开发等诸多领域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而推动中俄、中蒙、中朝、中韩等双边国际关系的发展。总之,流域文明的研究范式能够有效促进和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其五,流域文明研究范式对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以流域文明的研究范式切入人类学的研究,即是对流域范围内人地关系的探讨。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宇晓教授指出:“流域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以水为纽带,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本体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作为人类群聚与繁衍的最基本自然单元,多维立体化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景象,深刻地反映了人地关系伴随着自然与人为因素改变而产生的波动、对立与调和。有学者即已深刻地指出:“流域既是自然资源、人类群体聚散认同、人地关系行为、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记忆的群集单元,也是物质及能量流动、人口迁移和文化传布的廊道线路,更是人—地—水交叉互动的复合系统,具有面上的区域性、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和协同演化特征。因此,以流域为视角,可以更好地将点、线、面三个层次上的研究融为一体,实现人类学的整全观。”[2]“流域”视角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呈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对松花江流域下游赫哲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其所撰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划时代宏著。该书以松花江下游为自然主线,对赫哲族文化风俗进行研究,展现了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对“流域文明”研究范式的自觉运用和意识的觉醒。20世纪70年代,由张光直教授组织领导的“台湾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则是流域人类学在现代学术视阈下的一次积极实践。到目前为止,流域人类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根据不同流域而自成体系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民族生态和人类社会的重要研究范式,并为当代流域环境开发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东北流域文明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它强调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强调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而产生的文明和文化的不同,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汇、融合与碰撞。
总之,流域文明正是当今区域史与“整体史观”思潮下,最新研究范式的呈现。其优越性、创新性与实用性,已经在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学、跨国区域社会发展与交流合作等多个学术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研究范式,既冲破了固有思维和研究理念对学术发展的制约和禁锢,同时也打破了现实中行政界线和国境线对区域历史文化的阉割和肢解,对淡化界限意识、缓和国家和民族的情绪对立、消弭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我们得以以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态度,去尝试重建古史、重建区域。诚如葛兆光所言:“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3]因此,唯打破陈旧的窠臼,才能实现伟大的创新。学术界应加强交流,通力合作,建立以流域文明为核心,多学科并联、多领域交融的“流域学”。这一综合性学科的建立,将最大限度地统筹和整合各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并还原人类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对学术界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价值。
[1] 中国学者称“新开流文化”,俄学者称“鲁德纳亚文化(孔东文化)”,故学术界一般也称之为“新开流—鲁德纳亚文化”。
[2] 曾江:《作为方法的流域:中国人类学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月8日。
[3]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