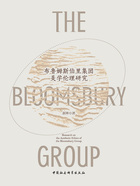
(三)发展脉络
这个以伦敦中西部的布鲁姆斯伯里区[37]为活动中心(1905—1939)并因此得名的智识团体,以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界,分为“老布鲁姆斯伯里”(Old Bloomsbury)、“后布鲁姆斯伯里”(Later Bloomsbury)[38]与“遗布鲁姆斯伯里”(Posthumous Bloomsbury)前后三个时期。
集团确切的成立时间,众说纷纭[39]。一说为1904年,是年,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作家、批评家、编辑、哲学家)去世,凡尼莎和索比、弗吉尼亚、阿德里安出售位于肯辛顿海德公园门(Hyde Park Gate)22号的老宅,迁居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46号,索比的众剑桥同窗好友应邀而至,与凡尼莎、弗吉尼亚相识,成为家中常客。虽然从上流社会体面的肯辛顿搬至职业中产阶级简陋的布鲁姆斯伯里,令两位同母异父的兄长和亨利·詹姆斯、哈代等斯蒂芬家一众思想保守的亲友大为震惊,甚至引以为耻;但从阴暗沉闷逼仄的海德公园门逃向明亮喧闹宽敞的戈登广场,却令年轻的斯蒂芬们终获自由,焕发新生,开始尝试“各种实验和变革。……一切都将是新的;一切都将不同。一切都在实验中”[40]。又一说为1905年,是年,除凡尼莎成立“星期五俱乐部”(Friday Club)[41]外,索比开始举办“星期四晚间聚会”(Thursday Evenings/Nights)[42],与三位手足及剑桥友人无所顾忌地讨论文学、艺术和哲学,探究美、善和真实的本质,特别是由于斯蒂芬两姐妹的加入,众人“交谈的语气和内容为之一变,不再是剑桥高深的逻辑和严峻的智识主义,取而代之以轻松幽默的谈话。抛开讲话的各种仪式套路,最终甚至连性这一维多利亚时代最为禁忌的话题都成了他们讨论的主要论题之一”[43]。弗吉尼亚说,“就我而言,这些星期四的晚间聚会是之后——在报纸上和小说里,在德国和法国,甚至我敢说,在土耳其和廷巴克图——被称作‘布鲁姆斯伯里’的那个团体的萌芽”[44]。还有一说为1906年,是年,备受众人尊崇爱戴的索比罹患伤寒溘然病逝,哀痛的亲友们并未因他的去世四散分离,反因对他念念不忘的共同思忆而愈发紧密相连。
1910年5月,爱德华七世去世,十年的爱德华时代宣告结束。同年11月8日到次年1月15日,弗莱在德斯蒙德的协助下在伦敦的格拉夫顿画廊(Grafton Galleries/Grafton Gallery)举办名为“马奈与后印象派画家”(Manet and the Post-Impressionists)的第一届后印象派画展,展出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德朗(André Derain)、毕加索等画家的画作,引起巨大轰动[45];1912年,弗莱在伦纳德的协助下举办第二届后印象派画展,展出画作囊括法国以及英国和俄罗斯画家的作品[46]。1913年3月和7月,弗莱先后成立“格拉夫顿集团”(The Grafton Group)[47]和创办“欧米伽艺术工场”(The Omega Workshops)。相比于文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活动,集团最先在视觉艺术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惊世骇俗、恶评如潮的后印象派画展到标新立异、备受追捧的“欧米伽艺术工场”融后印象派、立体派和野兽派于一体的应用设计,从凡尼莎、格兰特和弗莱的后印象派绘画作品到克莱夫和弗莱推崇形式主义的艺术批评,集团的精神气质和理念精髓得到了最为形象直观的展现。
1910—1914年,“‘布鲁姆斯伯里’大扩展、大发展,生活中充溢着各种各样的趣味、期望和扩展”[48]。然而,属于以集团为代表的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张扬、奋发向上的乔治时代,很快便被“一战”骤然打断。“一战”是集团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同时,“一战”期间也发生了一系列对集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对汹涌的爱国主义情绪的洪流,集团旗帜鲜明地坚持早在1910年2月弗吉尼亚、阿德里安和格兰特在“无畏号战舰恶作剧”(The Dreadnought Hoax)事件中便已流露出的和平主义观点,为此,克莱夫、格兰特、戴维·加尼特、利顿、伦纳德等人离开伦敦,或是作为“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下乡务农以“自愿性服务”替代应征入伍,或是因身体健康原因免服兵役隐遁乡间;为此,集团失去了一些朋友(如鲁伯特·布鲁克),结识了另外一些朋友(如罗素、劳伦斯、曼斯菲尔德和莫瑞尔夫人),同时保持甚至巩固了自身内部的友情。1917年,在战争的尾声中,伍尔夫夫妇在伦敦南部的里士满创办“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继“欧米伽艺术工场”之后,“霍加斯出版社”成为集团又一个活动中心和新成员、新朋友的聚集地;年底,伦纳德与奥利弗·斯特雷奇(Oliver Strachey)成立“1917年俱乐部”(The 1917 Club)[49],在集团成员之外汇集了一批左派政治人士。然而,如同英国文化的其他各个方面,集团始终未能从战争造成的巨大混乱中完全恢复过来,而守护文明、反对战争的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也将伴随大多数集团成员终生。
“一战”的爆发并未终结集团,相反,“战时和战争刚一结束,它便抓住时机一举攻城略地”[50]。“一战”期间,集团的作家们开始发力,成为代言集团的新声,1915年弗吉尼亚出版处女作《远航》(The Voyage Out),1918年利顿出版“新传记”第一部《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Cardinal Manning,Florence Nightingale,Dr.Arnold,General Gordon),均大获成功。战后,由于良心拒服兵役,集团遭到外界的谩骂和贬损,但也正因为此,虽然在战时四散飘零,集团却并未像其他许多将自己的年轻人送上战场的文学艺术团体一样遭到战争的摧毁,而是在度过严冬后,迎来二三十年代的盛大绽放。1920年代,“邓肯·格兰特是‘伦敦艺术家协会’(London Artists’ Association)[51]的核心人物;罗杰·弗莱的讲座吸引了大量听众,场场座无虚席;利顿·斯特雷奇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书赢得越来越多的好评”[52]。卓然出群的集团塑造了“1920年代的主导性主题”,战后的智识品格是相信私人世界,“知识分子对他们自己的心灵状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价值观是美学的而非道德或伦理的”[53]。1922年,一本美国期刊登载了一篇名为《布鲁姆斯伯里与克莱夫·贝尔》(“Bloomsbury and Clive Bell”)的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利顿、弗吉尼亚、凡尼莎、凯恩斯和格兰特,首次使用“布鲁姆斯伯里”一词[54]。然而,此后,这一称谓开始频繁出现在报刊书籍中,成为一个令集团成员大为恼火的侮辱性新闻用语[55],“整个世界紧紧包围,充满敌意,‘布鲁姆斯伯里’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活动、无法扩展、无法成长的没有变化的环境”,“……‘布鲁姆斯伯里’已辉煌不再。它消解在新世界和如今我们称之为‘20后’的年轻一代人中”[56],而到1930年代,连集团的孩子昆汀也开始“批判它——而我的朋友们甚至批判得更猛烈”[57]。尽管凡尼莎多年后的回忆依然充满沮丧和愤懑,但事实上,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集团才真正成为公共团体,成为伦敦乃至整个英国文学、艺术、思想与文化生活的中心。
集团确切的成立时间不明,同样,它确切的结束时间也模糊不清,一说为1939年(“二战”爆发)安吉莉卡21岁生日聚会后,另一说为1964年克莱夫去世后。[58]而事实上,当集团核心成员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在各自领域先后迈入辉煌期,开始闻名于世,发挥集团最具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影响力时,私人团体属性的“布鲁姆斯伯里”便已然“老”去,甚或“已然停止存在”[59],成为早期核心成员的集体记忆。1920年,在前一年便已停业的“欧米伽艺术工场”最终清盘,戏称集团成员为“布鲁姆斯伯里花浆果”(Bloomsberries)[60]的莫莉成立“回忆俱乐部”(The Memoir Club)取而代之,以供除西德尼-特纳之外的十三位集团创始成员在战后重聚,坦诚真言,共同怀想“老布鲁姆斯伯里”的情谊与信念。一直绵延到克莱夫去世时方告结束的“回忆俱乐部”[61]历经了集团从“后布鲁姆斯伯里”时期的鼎盛到“遗布鲁姆斯伯里”时期的新生,在成员的反复追忆与缅怀中,维系着集团长达六七十年、跨越两代人之久的绝对信任的亲密关系,见证了集团珍贵遗产持久不灭的薪火相传。[62]
由于组织松散、边界模糊、成员迥然相异到甚至弗吉尼亚[63]、伦纳德、克莱夫和凡尼莎均曾否认过其存在,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共同体”(creative community)[64]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在同一性,究竟是否是一个同质的实体,争议颇多。或认为“‘布鲁姆斯伯里’没有统一的哲学,……但却拥有美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共同理念”[65];或指出尽管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但集团成员在思想上并不同质,艺术观、文学观和政治观也并非完全一致[66];或发现集团成员没有共同的特质、信念和志向,“只是在个体意识、外在自然、孤立状态(isolation)、时间、空间、爱和死亡等方面有着彼此交叠、相互关联的相似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67]。而究其本质,毋宁说没有总体立场、摒弃共同教义或原则但却聚拢在一起、有效撒播并整合不同立场的集团(常被比喻为“大杂烩”[hodgepodge]、“鸡尾酒”[cocktail]、“混合物”[amalgam]等),更像是“一个字面和隐喻双重意义上的交汇点,一个跨学科的思想和艺术的纽结,在此,各种异端的现代先锋观念时而交融时而交锋,有共鸣也有论争”[68]。
尽管禀性、才情、兴趣、观点、专业、成就乃至令人失望的不足之处各异,尽管拒绝被记者、评论家和权威人士不负责地贴上“布鲁姆斯伯里”的统称标签,但因阶级惯习(habitus)、家族谱系和个人特质而意气投合,并进而因共同的教育背景、职业性质和活动空间[69]而结成终生友情的集团成员,整体上依然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倾向与明显相似的哲学、艺术和社会信念,表现出一种独特而复杂、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维特根斯坦语)或“有机统一性/整体性”(Organic Unity/an Organic Whole,摩尔语)的精神气质:(家世、智力、才华上的)优越、超脱、特立独行;沉思、交谈、侧身践行;拥有健全的精神世界、深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审美感知、强烈的怀疑意识,以及高超的想象力、革新力和创造力与敏锐的分析力、判断力和批判力。具言之,集团成员挑战传统、权威、正统和常规,反叛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制度、道德和习俗;蔑视名利权势,批判资产阶级庸俗市侩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信奉不可知论,倡导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崇尚才智,强调直觉、感性和抽象思辨,崇拜法国文化,专注高雅品质,追求爱美真的愉悦享受、绝对价值和至善理想;标举兼容再现性和表现性的形式(主义)美学,引领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文学,革新美学品味;推崇基于理智与坦诚的友情伦理,主张性开明与性宽容,探索同性恋、自由的爱与开放式的婚姻,创新日常生活模式(pattern of life)和言谈举止风格(mannerism),塑造既满怀爱意又保持独处、既不拘礼仪又严于克己的新型个人关系;坚守基于个体或小团体道义感的公共良知和社会正义,反对无知、平庸、贫穷、野蛮、帝国、战争、暴力、暴政、剥削、压迫、压制、偏见、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反感(战时的、黩武的、恶毒的、普遍敌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抗议种族化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扬政治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女性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关心并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投身社会改革。克莱夫曾这样描述他们的信仰,“爱好真理和美,宽容并且具备真实的精神,对无聊的东西深恶痛绝,有幽默感而又有礼有节,好奇,厌恶平庸、粗暴和虚荣的东西,不迷信,不假装正经,毫不畏惧地接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畅所欲言,关心艺术教育,蔑视功利主义和无知,总之,是热爱甘美的和光明的东西”[70]。弗朗西丝·帕特里奇回忆道,“他们并非一个团体,而只是因为生活态度一致而聚集在一起,恰巧他们中的很多人彼此或是朋友或是爱人。如果说他们不受习俗的羁绊似乎有些不妥,好像他们对社会规则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对习俗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思想中。他们在‘一战’期间都属于左翼人士,提倡无神论和和平主义(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在‘二战’中也持有相同的主张);他们热爱艺术和旅行,爱好读书,对自己的近邻法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除了钟爱自己的职业如写作、绘画、经济学研究,他们还喜欢谈话,并且乐此不疲,无论是抽象深奥的社科知识,还是俗不可耐的街谈巷议,都在他们的话题之列。我也从来没有——即使在剑桥大学时——遇到过像他们这样崇尚理性……诚实、创造性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依然如此。……说他们之所想……直言不讳”[71]。
[1] 根据S.P.罗森鲍姆(Stanford Patrick Rosenbaum)的观点,“由于集团并非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流派,因此,用circle和set两词指称集团显然太过严格限定,特别是后者一般常用于社会关系。相比之下,意义较为宽松的group一词反而似乎更为准确”(Victorian Bloomsbury:Vol.1: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7,p.3)。因此,本书采信The Bloomsbury Group的表述方式,译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并为免烦琐,除引文、书名、篇名和语境不清的情况之外,一般简称为“集团”。
[2] Victoria Rosner,“Introduction”,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loomsbury Group,ed.Victoria Rosn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16.
[3] Jane Goldma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32.
[4] Regina Marler,Bloomsbury Pie:The Making of the Bloomsbury Boom,London:Virago Press,1997,p.5.
[5] Regina Marler,Bloomsbury Pie:The Making of the Bloomsbury Boom,p.6.
[6] Regina Marler,“Bloomsbury's Afterlife”,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loomsbury Group,pp.215-230.
[7] Gabrielle McIntire,“Modernism and Bloomsbury Aesthetics”,in Virginia Woolf,ed.James Acheson,London:Palgrave,Macmillan education,2017,pp.60-73.
[8] Victoria Rosner,“Introduction”.
[9] Sara Blair,“Local Modernity,Global Modernity:Bloomsbury and the Places of the Literary”,in ELH 71,No.3(Fall,2004),pp.813-838.
[10] Silke Greskamp,“Friendship as ‘A View of Life’:The Bloomsbury Group an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in Modernist Group Dynamics: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Friendship,eds.Fabio A.Durão and Dominic Williams,Newc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8,pp.71-94.
[11] Raymond Williams,“The Bloomsbury Fraction”,in Culture and Materialism:Selected Essays,London & New York:Verso,2005,pp.148-169.
[12] Michael Holroyd,“Bloomsbury and the Fabians”,in Virginia Woolf and Bloomsbury:A Centenary Celebration,ed.Jane Marcu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7,pp.39-51.
[13] lion在英语中常喻指“有影响力、有魅力的重要人物,受人钦敬的名人、名士”。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0年12月23日写给Barbara Bagenal的信中将集团成员聚居的布鲁姆斯伯里区戈登广场比喻为“动物园中的狮屋”(lions house at the Zoo),将聚居于此的集团成员比喻为“危险、相互猜疑、充满吸引力和神秘感”的“狮子”(“Letters”,in The Bloomsbury Group: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rev.edition,ed.S.P.Rosenbau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5,pp.62-65)。里昂·埃德尔(Leon Edel)在其《布鲁姆斯伯里:众狮之屋》(Bloomsbury:A House of Lions,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mpany,1979)一书中借用了这两个意象。
[14] 因集团成员以及与集团有关的圈外人士相互之间多有亲缘或姻亲关系,故同姓者众多。为求简洁,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集团十一位核心成员,首次提及后,无同姓者,单称其姓,如弗莱、格兰特和福斯特。有同姓者,或仅称其名,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按学界惯例称其伍尔夫而称弗吉尼亚,以免与伦纳德·伍尔夫混淆;或单称其姓,如凯恩斯,虽后文会提及其弟杰弗里·凯恩斯,但因中文中一般不称其约翰或梅纳德,故尽管有同姓者,依然称其姓氏。同时,以免混淆,除语境清晰和出现频率较高的情况之外,其他人名,有同姓者,始终采用全称;无同姓者,按惯例,或全称,或单称姓或名。最后,出现于引文、书名、篇名中的人名以原文为准。
[15] Leonard Woolf,Beginning Again: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1911-1918,London:Hogarth Press,1964,p.22.
[16] 戴维·加尼特可能是1915年通过“新异教徒”开始与集团建立起长期亲密关系的。最初,戴维在集团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之后他与集团各位成员的密切交往或许成了“新异教主义”(Neo-Paganism)对集团最持久的一种影响(S.P.Rosenbaum,Georgian Bloomsbury: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1910-1914,Vol.3,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6)。
[17] 斯蒂芬·汤姆林的代表作是1931年完成的弗吉尼亚胸像,现安放在查尔斯顿农舍的工作室内。这座石膏胸像曾被多次浇铸复制,一座现安放在僧舍的花园里,一座现收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ondon),另一座于2005年6月26日由“大不列颠弗吉尼亚·伍尔夫协会”(Virginia Woolf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安放在1924—1939年弗吉尼亚长期居住的塔维斯托克广场(Jane Goldma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p.22)。但弗吉尼亚自己并不喜欢这座胸像,因为被雕塑的过程“让她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形象,一个东西:她憎恶这种感觉,甚至甚于被画成画像”,尽管现在陈列在查尔斯顿工作室的这座胸像事实上极富表现力,令人印象深刻(Hermione Lee,Virginia Woolf,New York:Alfred A.Knopf,1997,p.622)。除弗吉尼亚之外,汤姆林还曾为利顿、格兰特和戴维·加尼特等集团重要人物雕塑胸像。
[18] 早期被视作集团成员(严格意义上,应是早期友人)的还有:杰拉德·舍夫(Gerald Shove)、H.T.J.诺顿(H.T.J.Norton)、安格斯与道格拉斯·戴维森兄弟(Angus and Douglas Davidson)、塞巴斯蒂安·斯珀特(Sebastian Sprott)、F.L.卢卡斯(F.L.Lucas)、西德尼·瓦特罗(Sydney Waterlow)、贺拉斯·科尔(Horace Cole)、马杰里·斯诺登(Margery Snowden)、J.T.谢泼德(J.T.Sheppard),以及乔治(“达迪耶”)·赖兰兹(George W.R.[“Dadie”]Rylands,戏剧导演)、圣约翰(玛丽)·哈钦森(St.John[Mary]Hutchinson,克莱夫的情人)、查尔斯·丁尼生(Charles Tennyson,诗人丁尼生的孙子),等等。
[19] 关于“(老)布鲁姆斯伯里”最后落幕的标志,除“一战”外,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是利顿胃癌病逝,另一种认为是弗吉尼亚自溺身亡。
[20] David Gadd,The Loving Friends:A Portrait of Bloomsbury,London:The Hogarth Press Ltd.,1974,p.191.
[21] “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1月,鼓励英国知识分子讨论社会主义理想,探索将社会主义原则适用于英国现有政治体制的途径。1900年,费边社成为新成立的“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更名为“工党”)的会员组织。费边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民主方式渐进式地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萧伯纳、韦伯夫妇、格雷厄姆·华莱士、H.G.威尔斯等,伦纳德也是主要社员之一。
[22] 除薇塔之外,弗吉尼亚的另外两位女性密友是薇尔利特·狄金森(Violet Dickinson)和埃塞尔·史密斯(Ethel Smyth,歌剧作曲家、女权运动领军人物)。
[23] 无论是薇塔与丈夫哈罗德引起集团兴趣、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还是弗吉尼亚与薇塔的恋情,都不应遮蔽尼克尔森夫妇与集团在阶级出身、教育背景和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异(S.P.Rosenbaum,Victorian Bloomsbury:Vol.1: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pp.5-6)。
[24] “奥登一代”,又称“奥登集团”(The Auden Group)或“30年代诗人”(The Thirties Poets),一个用以称呼1930年代活跃在英国文坛、出身牛津剑桥、思想普遍左倾的诗人和小说家的方便称谓。除上述三人,公认的成员还包括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和西塞尔·戴·刘易斯(Cecil Day Lewis);此外,奥尔德斯·赫胥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约翰·莱曼(John Lehmann),以及燕卜荪和朱利安·贝尔,也常被认为属于“奥登时代”(The Age of Auden)。
[25] 1932年利顿病逝后,卡灵顿随即自杀。
[26] 1919年,毕加索与第一任妻子、芭蕾舞演员欧嘉·科克洛娃(Olga Khokhlova)随同佳吉列夫(Serge 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来到伦敦,对集团产生了个人影响。他为莉迪亚·罗珀科娃作画,与弗莱和之前就结识的克莱夫一同用餐,参观“欧米伽艺术工场”。
[27] “贵格会”,又名“教友派”“公谊会”(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Society of Friends or Friends Church)。“贵格会”教义包括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平等、互爱、宽容,提倡团体生活,等等。
[28] Stephen Michael Tomkins,The Clapham Sect:How Wilberforce's Circle Transformed Britain,Oxford:Lion Hudson,2010,p.12.
[29] Leonard Woolf,Sowing: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1880-1904,London:Hogarth Press,1960,p.160.
[30] Raymond Williams,“The Bloomsbury Fraction”.
[31] 为区别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lib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素质教育),直译为“自由教育”。
[32] “子夜社”之前,利顿、伦纳德和索比曾成立“X社”(The X Society),每周六晚聚会,一起阅读除莎士比亚之外的16世纪、17世纪戏剧家的剧作、易卜生和萧伯纳的现代戏剧,以及他们自己创作的剧本。同时,利顿、伦纳德和索比还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莎士比亚社”的成员。
[33] “剑桥使徒社”,又称“剑桥清谈会”(The Cambridge Conversazione Society),成立于1820年,为剑桥大学学生社团,有特定的行话和仪式,规定对外绝对保密,对内绝对坦诚。因成立之初带有鲜明的福音派色彩,故成员称为“使徒”。每届12名成员,主要由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圣约翰学院等学院智力超群且身世显赫的本科生组成。每年在新生中暗中选拔,候选者称为“胚胎”(embryo),通过考察其言行,最终仅甄选3名最佳者入选,一旦入选,“使徒”身份终身保留,毕业后的“使徒”称为“天使”。每周六晚,“使徒社”成员秘密聚会,畅谈纵论,从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历史到真理、上帝、伦理等“严肃问题”(serious questions),乃至日常生活话题,无所不及。1890—1914年为“使徒社”最健旺的时期,其历届杰出成员除这一时期的上述集团成员(詹姆斯·斯特雷奇和朱利安·贝尔后分别于1906年、1928年入选)及其圈外友人摩尔、罗素、迪金森、维特根斯坦、鲁伯特·布鲁克、屈维廉外,还包括维多利亚时代桂冠诗人丁尼生,19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等等。
[34] Henry Sidgwick,A Memoir by A.S.and E.M.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06,pp.34-35.
[35] Peter Allen,The Cambridge Apostles:The Early Ye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8.
[36] William C.Lubenow,The Cambridge Apostles,1820-1914:Liberalism,Imagination,and Friendship in British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40.
[37] Bloomsbury一词字面上由bloom(观赏花卉)和bury(城堡、村镇)两个词根构成,赵毅衡与董桥分别意译为“花镇”与“百花里”(旅居英国数十年的著名作家、翻译家桑简流先生[原名水建彤,1921—]最先将Bloomsbury译作“百花里”,董桥先生因袭妙译)。布鲁姆斯伯里区大规模规划建设开始于18世纪,最初为富商的高档住宅区;19世纪起逐渐沦为外国人和伦敦大学学生的公寓,以及各类绅士社团(gentlemanly society)的办公室;虽豪华不再,但始终保持着基本的体面,因此,到20世纪初,逐渐取代切尔西(Chelsea)成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聚居地。如今,区内已遍布花园广场、博物馆、大学、图书馆、画廊和医院,大英博物馆主馆、伦敦大学行政楼(Senate House of London University)、库图尔德学院画廊(Courtauld Institute Galleries)、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Dramatic Art)均坐落于此。
[38] 伦纳德又将“老布鲁姆斯伯里”或“老布鲁姆斯伯里”+“后布鲁姆斯伯里”称为“原布鲁姆斯伯里”(ur-Bloomsbury),前缀ur-为“原始、原初”之意。
[39] 伦纳德认为集团开始于他从锡兰回到伦敦与克莱夫、凡尼莎、弗吉尼亚等人重聚的1911年,因为,从地理上讲,当时核心成员并非全都住在布鲁姆斯伯里区,直到大约十年后(1912—1914),集团已完全成型,成员们才全部住进该区(“Old Bloomsbury”,in The Bloomsbury Group: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pp.141-146)。
[40] Virginia Woolf,“Old Bloomsbury”,in The Bloomsbury Group: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pp.40-59.
[41] “星期五俱乐部”主要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艺术展览,以及绘画和其他美术门类,成员不仅包括凡尼莎的亲友还聚集了多所伦敦艺术院校的毕业生。1905年10月13日,成员在戈登广场46号首次正式聚会,11月首次共同举办画展。俱乐部的聚会和画展一直持续到1914年。
[42] 1905年2月16日,索比在戈登广场46号第一次“在家中接待朋友”(at homes),1907年秋,阿德里安和弗吉尼亚在菲茨罗伊广场29号恢复因索比去世中断的聚会。参加“星期四晚间聚会”的这群朋友组成了“一战”前“老布鲁姆斯伯里”的核心。
[43] Ulysses L.D'Aquila,Bloomsbury and Modernism,NY,Bern,Frankfurt am Main & Paris:Peter Lang,1989,p.6.
[44] Virginia Woolf,“Old Bloomsbury”.
[45] 1924年,弗吉尼亚在其广为流传的名文《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中宣称:“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发生了变化。”第一届后印象派画展无疑是促使弗吉尼亚做出这一经典断言的核心事件之一。
[46] 两届画展向英国公众介绍了1890—1910年法国艺术的变化。画展名称中的“后印象派”一词涵盖若干欧洲绘画传统:修拉和毕沙罗的新印象派、立体主义、野兽派,以及高更与“阿望桥村派”(Pont-Aven),等。
[47] “格拉夫顿集团”,一个1913—1914年在伦敦“阿尔卑斯画廊”(The Alpine Gallery)展出画作的画展社团,前身是凡尼莎的“星期五俱乐部”,成员除弗莱、凡尼莎、格兰特外,还包括法国雕塑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画家刘易斯、弗雷德里克·埃切尔斯(Frederick Etchells)、威廉·罗伯兹(William Roberts)和爱德华·沃兹沃思(Edward Wadsworth)。弗莱希望借集团形式为进行后印象派绘画风格实验的画家提供展出画作的机会,并曾邀请美国犹太移民雕塑家、画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俄罗斯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参展。
[48] Vanessa Bell,“Notes on Bloomsbury”,in The Bloomsbury Group: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pp.110-111.
[49] “1917年俱乐部”,成立于列宁十月革命(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之前的1917年10月,成员包括伍尔夫夫妇和拉姆齐·麦当劳、J.威奇伍德等民主社会主义者。1917年12月19日,全体成员首次聚会。
[50] Frank Swinnerton,“Bloomsbury:Bertrand Russell,Roger Fry and Clive Bell,Lytton Strachey,Women,Virginia Woolf”,in The Georgian Scene:A Literary Panorama,New York:Farrar & Rinehart,1934,pp.339-377.
[51] “伦敦艺术家协会”在凯恩斯的大力倡议下成立于1926年。成员不限于画家,还包括“欧米伽艺术工场”的装饰艺术家们。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确保艺术家可以通过在每年圣诞节前举办的定期画展上售卖自己的作品从而获得一份薪酬补偿。“二战”爆发中断了协会的蓬勃发展。
[52] Janet Watts,“Dear Quentin:Janet Watts Interviews Mr.Bell of Bloomsbury”,in Virginia Woolf Quarterly 1,No.1(Fall,1972),pp.111-116.
[53] G.H.Bantock,“The Private Heaven of the Twenties”,in Listener 45(March 15,1951),pp.418-419.
[54] Richard Shone,Bloomsbury Portraits:Vanessa Bell,Duncan Grant,and Their Circle,Oxford:Phaidon,1976,p.15.伦纳德指出,事实上早在外界之前,集团内部就已经在使用这一称谓了(Beginning Again:An Autobiography of Years,1911-1918)。
[55] 对集团更具侮辱性的另一个称谓是Bloomsbuggery(布鲁姆斯伯里鸡奸团)(Phyllis Rose,Woman of Letters:A Life of Virginia Woolf,New York:Oxford UP,1978)。
[56] Vanessa Bell,“Notes on Bloomsbury”.
[57] Janet Watts,“Dear Quentin:Janet Watts Interviews Mr.Bell of Bloomsbury”.
[58] Jan Marsh,Bloomsbury Women:Distinct Figures in Life and Art,New York:Henry Holt & Co.,1996,p.158.
[59] Desmond MacCarthy,“Bloomsbury,An Unfinished Memoir”,in The Bloomsbury Group: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pp.65-74.
[60] 区别于Bloomsberry这一戏称,对集团成员不带感情色彩的一般性称谓是Bloomsburian、Bloomsburyan、Bloomsburyite、Bloomsburys(布鲁姆斯伯里人)等。
[61] 伦纳德认为“回忆俱乐部”最后一次聚会是1956年,尽管当时在场的成员有十人,但在世的集团早期核心成员仅余凡尼莎、克莱夫、格兰特和他四人(“The Memoir Club”,in The Bloomsbury Group: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pp.153-154),西德尼-特纳虽然在世,但早已退圈。
[62] S.P.Rosenbaum,Georgian Bloomsbury: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1910-1914,Vol.3,p.216.
[63] 根据斯蒂芬·斯彭德的记述,弗吉尼亚根本不喜欢“布鲁姆斯伯里”这个名字。有一次读到他书中提到了这个名字,弗吉尼亚还威胁说也要叫他、威廉·普洛默和他们那时同住在伦敦麦达维尔区的亲密邻居们“麦达维尔”(Maida Vale)(Stephen Spender,“A Certificate of Sanity”,in London Magazine 12,No.6[February-March,1973],pp.137-140)。
[64] Craufurd D.Goodwin,“The Bloomsbury Group as Creative Community”,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3,No.1(2011),pp.59-82.
[65] Victoria Rosner,“Introduction”.
[66] Quentin Bell,Bloomsbury,London:Futura Publications Ltd.,1974,pp.12-13.
[67] James M.Haule,“Introduction”,in The Bloomsbury Group Memoir Club,S.P.Rosenbaum,ed.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 Afterword by James M.Haule,London &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p.1-11.
[68] Kathryn Simpson,“Woolf's Bloomsbury”,in Virginia Woolf in Context,eds.Bryony Randall and Jane Goldm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70-182.
[69] 除布鲁姆斯伯里区,集团共同的活动空间还包括伦敦肯辛顿区(Kensington)、剑桥、英格兰南部乡间(东苏塞克斯郡:凡尼莎、格兰特、克莱夫和戴维·加尼特的查尔斯顿农舍[Charleston Farmhouse]、伍尔夫夫妇的阿什汉姆屋[Asheham House,距离查尔斯顿农舍仅一步之遥]和僧舍[Monk's House]、凯恩斯夫妇的蒂尔顿屋[Tilton House]、薇塔与哈罗德·尼克尔森夫妇的西辛赫斯特城堡[Sissinghurst Castle];西伯克郡:利顿、卡灵顿、凯恩斯等人的米尔屋[The Mill House];威尔特郡:利顿、卡灵顿和拉尔夫·帕特里奇的汉姆斯珀雷屋[Ham Spray House],以及牛津(莫瑞尔夫人的嘉辛顿庄园[Garsington Manor])、法国南部地中海渔港小城卡西斯(Cassis)等地。二三十年代,集团成员的生活“变得更富流动性和节奏性,但固定不变的工作地点依然还是在苏塞克斯、伦敦和法国南部”(Richard Shone,Bloomsbury Portraits:Vanessa Bell,Duncan Grant,and Their Circle,p.14)。
[70] 莫尼克·纳唐:《布卢姆斯伯里》,张小鲁译,瞿世镜编《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71]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他们的房子》,[加]S.P.罗森鲍姆编《回荡的沉默——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杜争鸣、王杨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