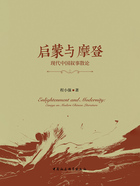
写在前面
2022年深冬,我的老友程小强,把他刚刚杀青的书稿《启蒙与摩登——现代中国叙事散论》从微信上发送给我,嘱我作序。对此,我并不意外,也没有推辞,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数次提出过作序之请。既然他心意已决,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然而,在他初提此事之时,我是深感意外的。这份意外,细究起来,大致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意外是:区区在下,何足蒙此错爱?我虽忝列大学中文系,却才疏学浅,始终未入学问之门,岂敢给他人写序?我自己都做不出什么学问来,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学术研究说长道短?我的序文只会给朋友的书“减分”,绝不可能“加分”呀!第二层意外是:我真的没想到,我在小强心目中竟然如此有地位、有分量!成年人都知道,“朋友”这一美好字眼早被滥用了,每个人的通讯录、朋友圈里都有成百上千个人来共享朋友之名,然而有朋友之实的,能有几人欤?小强显然是真心诚意地把我当成他的朋友,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写成的文稿毅然托付于我,还要把我的浅薄想法、粗陋文字同他的文稿绑定,共同流布世间,毫不顾虑我的序文可能拖累、埋没他的心血之作。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在所向无敌的现代性洪流里,小强这一选择,当然是极其独异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在他这个不易为人所理解的选择之中,难道丝毫没有魏晋风度之余响、《世说新语》之古风?
当我在案头翻开《启蒙与摩登》打印稿,未及拜读,便对着一盏孤灯,情不自禁地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了。我与小强结识、订交,大概已有八年了。2015年4月上旬(具体日期忘记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然一时兴起,应聘了某所“一本”院校的文学院。文学院所有专业的试讲,统一安排在一个下午。应试者逐一进入面试现场,去接受评委们的集体审视,其余人则在旁边的房间里等候。现当代文学专业排在最后,枯等之际,我和小强自然而然地聊起来,互通了姓名。我是最后一个进去讲的,天已经黑了。小强本来讲完就可以走了,但他没走,而是等我讲完,共进了晚餐,饭后还在宾馆里聊到午夜时分。分别后,我们各自回家等着录用结果。那一次,现当代文学专业录用名额是一个,竞争者则有三人,看上去并不算“白热化”,然而终究要产生两个失意者。小强认为我会被录取,理由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比他的母校陕西师大排名靠前一些。而我觉得,幸运儿一定是小强,因为他发表的文章更多,刊物级别更高。无论幸运儿是谁,反正都是出自我们这对“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语),总是值得弹冠相庆的。然而,事实证明我俩都想多了,幸运儿既不是我,也不是他,原来我们就是那两个必然要产生的失意者。真是哭笑不得!我呢,只好留在原工作单位,打消了变换门庭的妄想,小强则签约宝鸡文理学院,获得了他的第一份大学教职。“旧事真成一梦过”,这个亦真亦幻、略有意味的“华北应聘故事”匆匆落幕,消逝在时光深处,在我和小强的记忆中慢慢风干、泛黄。
宝鸡文理学院是所谓的“二本”院校,平台不高,资源有限,然而并不能限制有志气、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折戟于“一本”面试场的经历,并未让程小强一蹶不振,他迅速振作起来,立足于现实条件,潜心研读,埋头笔耕,很快就做出了成绩。他在2017年出版了22万字的《溯本与还原——现代文学名典再解读》,仅仅时隔两年,又推出了24万字的《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除专著外,他每年均可在CSSCI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不止一篇文章,身在高校的人都知道,这当然是并不亚于甚至高于专著的学术创获。至于在今日高教生态中高于一切的科研项目呢?国家社科基金,他立项了;教育部课题,他斩获了;陕西省的项目,他也拿到了。事实胜于雄辩,数据不会说谎,小强的学术产出,论质量,论数量,论效率,在国内“二本”中是居于前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其实,细究起来,完全可以说,在“一本”乃至“双一流”高校中,程小强的水准和成绩亦非广大“青椒”之常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来自大西北的小强,正如一个身强力壮的“麦客”,紧握着、挥舞着一柄趁手而锋利的学术之镰,快速行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黄土大塬上,刀光所至,“麦子”应声而倒,倒下的麦子越来越多,手中的镰刀越磨越利。我早就看不见他的尾灯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觍着脸给他写序呢?八年前“同台竞技”又一见如故的两个同龄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在我眼前打开的这部书稿,已经是程小强呈送学术界的第三部著作了。不难发现,该书具备显豁的主题,蕴含着鲜明的特色。其显豁主题,是主要聚焦于现代中国文学中两种重要的传统——启蒙话语/叙事、摩登话语/叙事,兵分两路,火力全开,阐发和厘清同一种话语/叙事的诸多面相、繁复流变。其鲜明特色,是精心选取有文学价值或文学史价值的作品或形象,去多角度、多侧面地勾勒和展现话语/叙事的多元化、丰富性。换言之,即:本书谈的是大话题,下的是细功夫,以话语/思潮为经、为“面”,以作品/形象为纬、为“点”,经纬交织,点面结合,织成一幅既尊重学术公论又颇具个人色彩的研究图景。坊间书籍多矣,其中亦不乏巨册长编,然而能够展现一种别具一格的研究图景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并不多见吧?
众所周知,“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位学者都不可能真正做到“文武昆乱不挡”。程小强之所长,不是对20世纪中国的启蒙、摩登话语/叙事做出全景画式的宏观把握,而是在广泛的涉猎中,凭借艺术鉴赏力和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有价值、有深度的文本,深入文本之肌理,探寻“文心”之所在,悉心提炼特定作家对于文学传统的“响应”方式,细致归纳文学话语对于具体文本的烛照之效。换言之,程小强更擅长通过个案之“点”去认识历史之“面”,凭借文本之“纬”去把握话语之“经”。这种学术特色,早在他的专著处女作《溯本与还原》中便初见端倪了。令人欣慰的是,他从未盲目追随学界的某些风潮,从未在千帆竞发的学术航道上迷失方向,而是始终保持了对自身优势的清醒认识,数年来不但未曾捐弃自己的学术强项,反而将其磨砺得更强了。当我打开《启蒙与摩登》,从目录到正文,从观点到论证,一页页、一段段、一行行,对我形成了持续而猛烈的冲击。小强涉猎之广、视野之大、用工之勤、阅读量之巨,都足以令我汗颜,令我肃然。通读全书之后,我觉得,小强早年确立的、发轫于《溯本与还原》的“细读”功力和“重读”志趣,在今天已然初步臻于洞幽烛远之境了。本书所研讨的作品,时间上兼顾现代、当代,空间上跨越西部、东部,文体上包含小说、散文,既有那些久经文学史淘洗、早已程度不一地实现了经典化的作品(包括《祝福》《离婚》《伤逝》《围城》《迟桂花》《小二黑结婚》《白鹿原》《长恨歌》等),也有未经时间充分考验的、文学史地位尚无定论的、虽未经典化却有典型化意义的文本(包括《纪念碑》《七步镇》《秦岭记》《刻骨铭心》《雁城谍影》《问道知源》《长沙白茉莉》等),各自汇聚为一个系列,大致构成了两种写作路向。
上述两种写作路向,相互之间当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实不可截然分开,但是它们仍然有区别、有偏重,正如两面不同的镜子,映照出文章作者不同侧面的学人风采——对经典名作的“重读”,优先体现的是程小强充沛的学术勇气,对非经典作品的“细读”,则首先折射了程小强开阔的文化眼界。如果一部专著同时展现了学术勇气和文化眼界,那么它就已经堪称合格的出版物了。然而,生逢伟大的新时代,无论是程小强本人,还是我也忝列其中的友人们,都不会允许他仅仅在合格线上止步。事实上,小强没有让诸位师友失望,他精心结撰的《启蒙与摩登》,在学术勇气、文化眼界之外,还展现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维度。序言毕竟不是审读意见书,无须面面俱到,限于篇幅也限于学养,我只选择对我触动较深者,挂一漏万地谈一两个方面。
触动我较深的第一个方面,是程小强书中那些层见叠出、新颖犀利、灵光乍现的大小论断。这些论断,有的是某一章或某一节的总论点,有的是某个章、节内部的一个分论点,有的是行文过程中的一个小结论,形式不一而足,但往往都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我不妨随手采撷几处以飨读者,以求达到管中窥豹之效——“解构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就是在否定启蒙时代”;“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人: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搞革命”;对贺老六之死,祥林嫂负有重大责任;《围城》的讽刺手法其实捉襟见肘,往往或无中生有,或无事生非,或以点带面;陈忠实缺乏创作天赋,《白鹿原》是他“强力为之”的结果……在《启蒙与摩登》中,此类新见、高论甚多,几乎达到俯拾即是的地步,而且这些见解绝不是脱口而出的“金句”,更不是凌空蹈虚、空穴来风,而是始终牢固而稳健地建立在翔实的材料、缜密的论证之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强对《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小芹母女形象的解析。我早年初读《小二黑结婚》,读到“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心里隐隐觉得不大对劲:小芹是抗日根据地新青年,“不跟人乱来”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怎么还值得赵树理刻意表扬一下?作为小说主角、正面形象,小芹的道德底线竟然只是“不乱来”,这底线是否太低了?小芹同男青年们“说说笑笑”,尤其令我不适,总觉得她不够文静和“矜持”,不大像我心目中玉洁冰清的“村花”。可见,所谓“问题意识”此时已在我心中萌发了,但是一向不求甚解的我把问题轻轻放过了,与学术发现失之交臂。然而,程小强却穷追不舍、不依不饶,他深究文本,小心求证,替我把如鲠在喉的话说出来了:“小芹与三仙姑不存在价值观、道德观上的根本分歧,小芹至少默许了其母与两代青年们的非道德化交往”,“如果没有小二黑出场,且不计革命因素,小芹大概率要沿着三仙姑的路子走下去”。这一论断,是令人信服的。
触动我较深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比第一个方面更重要,那就是程小强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问题的思辨,或曰对于历史小说应当“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追问。这一思辨和追问,折射了程小强的历史意识、责任伦理,反映了他审视和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与尺度”(朱自清语)。在本书中,小强讨论了王安忆的《长恨歌》、叶兆言的《刻骨铭心》、王小鹰的《纪念碑》、上官鼎的《雁城谍影》,这几部作品的共性是它们均与民国历史存在密切关联。《长恨歌》已然经典化了,历来的研究者基本众口一词,一致赞誉该书对张爱玲美学的传承和光大。然而小强却敢于力排众议,他尖锐地指出,《长恨歌》的人物、故事和风格,缩减了“上海摩登”的内涵,窄化了上海叙事的格局,抽空了历史的丰富性,那种“将颓靡情调演绎成摩登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并将之普泛化”的写法,仅仅提供了一种单一而偏狭的思想向度。小强严厉批评了《刻骨铭心》,将其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新样板”。他之所以下此断语,原因主要不是该书以大量笔墨描摹了风月之事、床笫之欢(这些当然能写,“文学是人学”,可以表现人性、人情的一切方面),而是在于“面对多数历史大事件时几乎蜻蜓点水般掠过,有关‘刻骨铭心’的历史叙事不到文本的十分之一”,历史风云不是作家严肃书写、正面表现的对象,而沦为升斗小民之蝇营狗苟的虚浮背景。其实,《长恨歌》《刻骨铭心》绝非文坛“孤例”,它们反映了几十年来恒河沙数的历史题材小说、影视剧的共同症候,代表了后革命/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叙事的“主流”写法。这种写法本来应当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支流”,然而因缘际会、世事难料,支流反而喧宾夺主,上升为主流。该主流的存在和盛行,远非一日矣,俨然已成为历史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被许许多多人无条件认同,也让有识之士深感无奈,若对其进行质疑和批判,反倒显得费力不讨好。然而,小强偏偏不怕费力不讨好,“虽千万人”,亦敢于对历史虚无主义亮剑。高度符合小强之期待的作品,是《纪念碑》和《雁城谍影》。这两部小说岿然屹立在《长恨歌》《刻骨铭心》对面,构成另一种更具精神高度、更有启示性的文学景观。《纪念碑》有效地瓦解了《长恨歌》文本中隐含的一个虚妄、片面的大前提——“上海叙事等同于上海摩登写作”,通过激情燃烧、生动鲜活的革命叙事,“全面继承并拓展了上海叙事的格局”,“反驳了摩登叙事长期以来的不负责任的妥协论调”。《雁城谍影》旨在“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审视”抗日战争,该书高度尊重史实,遵循写实法则,“严格依照47日作战的时间表”,工笔细描了慷慨悲壮的衡阳保卫战,“追念这场战争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还原每一个鲜活个体的生死细节”,对每一位“付出努力与牺牲的仁人志士给予应有之尊重”。《纪念碑》和《雁城谍影》共同的可贵之处,是让小说笔法服从、服务于史传精神,而非用小说笔法遮蔽、消解史传精神,成功地实践了“以历史拯救文学,进而决定文学价值的写法”,而这种写法正是程小强在他心中树立的精神标杆、创作圭臬。诚然,《启蒙与摩登》的大部分章节都对我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但是我必须承认,该书对于上述几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评论,对我的冲击尤其强烈,因为我从这些文字中体察到了一位以文学研究为“志业”者所持守的文化信念、家国情怀。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拥有文学知识、理论素养的文学从业者多矣,但能把知识、理论“内化”为信念、情怀并且顽强恪守的人并不多,我认为程小强就是后者。如果他同很多人一样,仅仅满足于知识的铺排、理论的操演,毫不在意文学生产的“用心”和“效果”,那么他就不会顶着压力突破“人情世故”,去指斥健在名家所写的《长恨歌》《刻骨铭心》。如果他同很多人一样,“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鲁迅语),那么他就会得过且过、就事论事,文本“写什么”就分析什么,把论文写出来且发表出来便万事大吉,根本不会去审视文本是“怎么写”的,更不可能因“怎么写”的问题而愤怒。订交以来,我已经拜读了程小强的多部著作、多篇论文,我可以确信,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沦为一个“万事不关心”、只汲汲于“成果”和数据的学术工匠,而是始终保持了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血性和良知,他不允许自己的科研事业异化为单纯应付考核、折算为KPI的功利化劳动,他力求让自己的论著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实现应有的精神价值。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文学如此,文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的文学研究,如果能够展现“以血书”般的真诚、炽热、高迈,那就一定可以受到读者的钟爱,赢得学界的青眼,绝不会落入“恨无知音赏”的境遇,毕竟“以血书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我这篇拉拉杂杂、言不及义的所谓序文,浪费了读者不少时间,终于到了收尾之际。任何一本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瑕,《启蒙与摩登》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整体观之,这确实是一部有创见、有分量、十分严肃的著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林,或可占据一席之地。本书在“技术”层面上可能存在某些小疵,但是无碍于全书的探索性、创造性、人文性,也无法遮蔽作者的思想光芒、学术激情、研究造诣。衷心感谢小强让我对书稿先睹为快,让我提前获得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但我显然还没有完全读懂、读透,待到书稿印成铅字之日,我一定会反复摩挲、一再重读,从中不断获得新的启悟。《启蒙与摩登》是小强学术之路上的又一块界碑,他当然不会驻留此处、裹足不前,他会迅速离开这块界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下一个路标。我对小强仁兄的学术道路深感钦佩,更对他的研究实绩衷心折服。我当然不可能跟上他的步伐,我所能做的且乐于做的,就是一直凝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
张慧强
2023年2月20日于重庆涪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