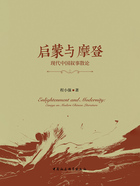
一 爱姑的出路:乡村宗法制的危机与调处[1]
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彷徨》起于《祝福》终于《离婚》,《祝福》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乡村人事命运的考察在《离婚》中得以重现,鲁迅叙写乡村女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情状,再现了启蒙时代重建现代人生的艰难。就研究史而言,对包括《离婚》在内的鲁迅部分小说解读上,各种阐释如思想启蒙的悲剧说、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论,“理”与“礼”的二律背反说,均抵达了《离婚》思考女性命运的片面深刻,如常见的以“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为代表的外部人事环境的悲剧归因法,就欠缺细致周密又合情合理地考察爱姑的悲剧发生学。又如爱姑和父亲庄木三在赴庞庄的水道上,“两个老女人”的念佛声从未受研究者关注。以鲁迅行文绝少闲笔的特点,为何会出现这些意义模糊的声音?鲁迅要借佛事佛语表达什么?再如多年来的研究一再误解爱姑且偏离文本重心,易纠缠于爱姑同意离婚与否。对《离婚》到底是一部悲剧还是一部轻喜剧,多年来的评价莫衷一是,大概在于疏于考察鲁迅小说写作的连贯性。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彷徨》集的收官之作,《离婚》继续使用《呐喊》《彷徨》集中气若游丝又一息尚存的以貌取人式讽刺,对此,如何做出合情合理更合乎人生实际的评价?这必然对文本的再解读提出更为质实的要求,一些重要细节必须被发现而非选择性忽略。
按,首先辨析一个从来皆对的事实——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爱姑不同意离婚,认为其大闹是为了能重返夫家[2],这是大错特错的想当然。如果爱姑想回到夫家,她肯定会在不离婚框架内选择较容易下的台阶来解决矛盾,那么庄、施两家之间的大闹意义无处体现,经济索赔和拆灶行为的动机更将无解。如多位论者认为,庄木三带六个儿子拆亲家灶的行为兹事体大,影响恶劣,在此语境下,爱姑回到夫家哪来好结局?所以爱姑直言“不贪图回到那边去”是可信的。庄木三与爱姑大闹夫家源于爱姑丈夫与一个小寡妇姘居,以一般乡土中国社会伦理传统而言,寡妇的道德地位肯定次于爱姑这样明媒正娶的女子,爱姑丈夫纳寡妇是爱姑的重耻,纳寡妇继而不要爱姑是耻辱的升级。最具耻辱感的是,连家境本不宽裕且武斗实力弱于庄木三的公公也斩钉截铁地支持儿子,这必然激起在本村以至更大范围如沿海地区都颇有名声的庄木三的斗志。耻辱尤其深重,深重的耻辱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才能洗刷,所以庄木三选择了拆灶这一带有侮辱和打压生存尊严的行为。饶是如此,施家父子也坚决要同爱姑离婚。一场离婚“已经闹了整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3],而闹了三年一直打架应有庄木三故意扩散影响的因素。于庄木三而言,一是借儿子多可大肆打闹以挽回颜面、洗刷耻辱,借以维护或可能发生动摇的乡村能人地位,小说开篇时众乡邻“捏着拳头打拱”与让座行为就是其地位没有受损的标志。至于庄木三说“这真是烦死我了”只是一个说辞,除了打架确实很烦人外,还有一点得了便宜仍卖乖的心理,他不想打架当然没人逼。二是从后来庄木三乐见多得一点赔偿金的贪钱来看,爱姑做寡妇后,庄木三不仅可拿到赔偿,且日后爱姑像祥林嫂一样再嫁时庄木三可收彩礼,可谓好事成双。所以,此番僵持的目的不是不离婚,而是爱姑要出完所有恶气的离婚附带诉求本来就无法实现,庄木三乐得既挣面子又得钱,二人诉求虽有错位,但都各怀心思谋求僵持。至于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纠缠,仍源于对鲁迅创作意图理解得不透彻。鲁迅将爱姑放到乡村宗法制仍在运行的大环境中,着重考量的是一个被离婚的女性在身受侮辱与损害之际的必要但又徒然的抗争悲剧及其成因。所以,除乡民八三之外,爱姑和所有参与此事的众人关注的焦点不在离与不离,而是如何离。
(一)公共舆论与乡民权力空间
鲁迅小说在叙事学上有着诸多重要贡献,其中受西方小说影响的场景结构是现代小说新范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离婚》将所有的故事发展、矛盾解决、人性呈现包括行动上的抗争与妥协全部置于场景结构内,使短篇小说的形式组织有效地推动了叙事,所谓“技巧圆熟”绝非虚言。《离婚》由两个场景组成:一是庄木三和爱姑从木莲桥头赴庞庄时的船舱内场景,二是七大人在庞庄的慰老爷家中为庄、施两家主持最后一次调解时的场景。借助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离婚》的这两个场景具备完整的公共空间要素,且形成了充分的公共舆论,鲁迅的写作意图以及塑造爱姑性格,均通过爱姑主导/参与公共舆论来完成。在第一个场景中,人物中心和事件中心合二为一,所谈离婚事件的舆论走向以爱姑的认知喜好为准,爱姑对舆论具备完全操控能力。在第二个场景中,人物中心和事件中心分裂,七大人借助威权走向人物中心,爱姑离婚事件继续成为事件中心,人物中心决定了事件走向。在后一场景中,七大人掌握了离婚事件的舆论主导权,爱姑与七大人及施家的冲突表面看来是爱姑对七大人主导公共舆论的质疑,深层则是爱姑破坏现有宗法秩序与七大人努力维护秩序的冲突。不凑巧的是,爱姑越过物质赔偿,力图质疑甚至否定维持中国封建乡村结构稳定近两千年的宗法制治理体系,在小说中表现为想讨一个说法、出一口恶气且不依不饶和死磕到底的形象。进而言之,爱姑所闹既是质疑一个不良家庭,更是借助乡村婚俗的合礼性来质疑施家父子提出“离婚”时所依据的封建男权中心的合理性。所以,当仅代表乡村治理合理性的慰老爷无法平息事态之际,只得请出代言现代法理的七大人来弥补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不足,继续维护封建宗法制主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而牺牲一个自身问题多多的乡村下层女性的利益且无须付出多少代价,就可化解乡村公共生活危机,使乡村复归平静,诚为七大人与慰老爷有效实施乡村治理的合情之举。
小说的第一个场景发生在爱姑与父亲庄木三由木莲桥头乘船同赴庞庄参加最后一次离婚调解会的船舱中。庄木三与爱姑甫一登船,众船客争相问候庄木三父女,接着让出四人座位,而庄木三同爱姑毫不客气就座。庄木三在乡村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如乡邻八三稍后陈述“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按照小说情节,是庄木三带了六个儿子去毁了亲家的灶,并不包括外人八三,八三所言“我们”有套近乎之嫌。另,庄木三所持长烟管的描写并非如部分论者所言的无意义,长烟管吸烟耗时费力,可吸烟者明显享受这个过程,烟雾可以吐纳得更久,长烟管看起来也更神气一些。这源于庄木三平日生活较为闲散,因为他有六个儿子可以分担各种杂事活计,他有资本背着手拿着长烟管检视督导;闲散的另一重意义在于,为了爱姑离婚事件,庄木三可以不厌其烦地与亲家进行两三年之久的拉锯战,施家则没有相应的人丁及时间优势。
一切坐定之后,一场断断续续的对话开始了。八三首先发言,他一方面和庄木三父女套近乎,一方面积极为庄木三父女分析当前形势:一是城里来的七大人介入此事,证明此事影响范围持续扩大,从七大人的身份看,七大人据持的威权为爱姑和众乡民所畏惧,此处惊愕意味着七大人的介入让事件不利于爱姑与庄木三;二是目前庄木三一家的行为已经够过分了,拆掉亲家灶是个标志——此事发生前,一口恶气没有出完,此事发生后,一口恶气应该能出完了,这是八三对事件的客观评判;三是爱姑即使(“况且”)回到施家继续做儿媳妇,“也没有什么味儿……”,这里的“味儿”指的是好滋味。八三有个潜台词,你庄木三如此坚持闹,即使爱姑回夫家去了,也没多大意思。八三理性又委婉地表达了劝和不劝离的看法,爱姑对此劝解明显不满意,她认为八三误解了自己:“‘我倒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八三哥!’爱姑愤愤地昂起头,说,‘我是赌气。’”[4]八三的思维明显停留在爱姑愿不愿意离婚的问题上,爱姑的“愤愤”源于对八三误认为自己大闹只是想再回夫家继续做媳妇而不得。事实上,爱姑在离婚事件启动后并未谋求返回施家,在乎的是在离婚既定情形下如何将恶气出足。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具备的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善良淳厚、温良恭让等良善品性,爱姑争强斗狠的性格豁然。爱姑坚持将恶气出到底的原因,可从其成长与生活环境来分析。小说对爱姑有限的几处描写,如钩刀脚显示其在辛亥革命以来有过放小脚经历,六个兄弟而无姐妹暗示其成长环境多见好斗、勇猛、剽悍、抗争等男性化风格,爱姑也确实具备相当的男性气质。至于其母从未出场,可能的解释有二:或在家中无地位,或因养育子女多耗损身心已亡故。总之,爱姑缺少一般母亲对女儿的母性滋养,多显言谈举止粗俗、形象气质差与缺少女性美等劣势。如对丈夫和公公处处以“小畜生”“老畜生”相称,随意随性粗野成风且毫不避讳,庄木三并无劝阻和制止证明其早已适应。这都无疑坚定了施家父子宁可选择一个懂事的寡妇也要休掉爱姑的决心。以鲁迅对小人物命运的一贯观察法,其不可能一味地将人物悲剧归因于各种外部因素,所以此番毫不避讳地呈现爱姑的缺陷,就符合鲁迅对悲剧人物命运的认知。
从离婚事件的进程看,丈夫找了个小寡妇借机要同爱姑离婚,公公全力支持。在此后的申诉中,爱姑一直强调自己是按礼仪明媒正娶进施家的,所以自己被离婚是夫家的错,且又被一个小寡妇替代了位置而倍加受辱。在爱姑的简单推理中,她既知已无法挽回婚姻,必然为挽回颜面而无休止大闹。所以爱姑认可慰老爷所言“走散好”的建议,却也同步否定了慰老爷将事件止于和平离婚的维稳努力,慰老爷的调解必然无效。无效源于慰老爷作为一般村镇士绅只能在宗法制乡村的合理性与合礼性框架内予以调解,面对爱姑基于合礼性考量的大闹行为与合法性的新诉求时必然束手无策。当启蒙行进艰难、现代革命远未兴起之际,乡村宗法制暂未退出历史舞台,新时代条件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结构性缺陷,要弥补这个缺陷,就必须借助新式人物来完成,七大人呼之欲出。
至于胖子汪得贵,可看作一类乡村看客。鲁迅小说叙事中“百无聊赖”的看客形象尤为引人瞩目,无聊看客每每将别人的灾难当作娱乐,汪得贵无疑属于“百无聊赖”的看客团成员。汪得贵的发言有两层意思:一是庄木三名望高且威名远播至沿海地区,二是庄木三谁都不怕。这明显就是“吃瓜群众不嫌事大”的心理。这类不怀好意的恭维反而正中爱姑下怀,坚定了爱姑继续死缠硬磕的信心:“要撇掉我,是不行的。”实际意思是:要这样撇掉我,是不行的。因为撇掉意味着事情结束,且只有垃圾才被称为撇掉,爱姑显然无法容忍自己像垃圾一样被撇掉,所以她坚持要“闹到他们家败人亡!”“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意为任何劝解都是无效的。对于爱姑的诉求,一听到可获赔偿就“头昏眼热”了的庄木三明显不支持,一句“你这妈的!”内涵丰富:爱姑惹得父亲颜面尽失,又一再纠缠于出恶气而不考虑实惠;爱姑一直将事情做绝,从来不知道中庸一点,让人无台阶可下,这令面子也要、实惠也要的庄木三不胜其烦。汪得贵对知书识礼之人一定会讲公道话做了一番言之凿凿的研判后,导致主导公共舆论的爱姑更忘乎所以了:
爱姑瞪着眼看定篷顶,大半正在悬想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慰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见过两回,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这种人本村里就很多,无非脸色比它紫黑些。[5]
爱姑也只有这点不计后果的盲动了,这为后来突然跌落的“反高潮”叙事埋下了伏笔。而小说中向来为论者所未注意到的两处细节描写就极富意味了:“船便在新的静寂中继续前进……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她们撷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船在继续的寂静中继续前进;独有念佛声却宏大起来;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爱姑一同浸在沉思里”[6]。“互视,努嘴,点头”是两位信佛老太对爱姑离婚事件的无声介入,她们身份卑微而不便坦言。“互视”表示心有契合而欲有表达;“努嘴”一词在不便表达之外内含否定之意,大概意思是看看她就这德行;“点头”表示认知一致而心领神会。哼起佛号、念佛声宏大起来令人遐想,此刻念佛是启示与规劝凡俗人事走上正途。佛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渡人渡己、出脱空华,佛也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及得饶人处且饶人,佛最反感在俗人俗事上一念执着,可爱姑偏偏就一念执着。静寂向来是思考人生的契机,思考意味着会让未来的行动更富理性。可对爱姑来说这就是对牛弹琴。在《离婚》的复调叙事中,要说哪一个声音最接近作者的声音,无疑就是这段规劝,但很显然它也是最无效的声音。
这是小说的第一个场景,公共舆论的形成由众船客围绕爱姑离婚事件的态度构成,随着爱姑断然拒绝八三合情合理的和平离婚建议而继续与夫家死磕,表面上的舆论杂音全部消失。《离婚》将爱姑置于一个复杂环境下考验其做出抉择的能力,而爱姑由此暴露出的浅薄、幼稚、不理性、无城府、易冲动都必然决定了离婚事件的走向。
(二)离散的权力空间与损害及悲剧
汪得贵投爱姑所好,全面肯定了爱姑和其父亲庄木三的威势,为其即将做出的抗争努力增添了相当勇气,第二个场景被顺利带出。在这个场景中,七大人为代表的威权中心与事件中心上的爱姑离婚事件并置,人物中心决定事件中心的[7]叙事设计从形式上决定了爱姑必然遭遇损害与侮辱。
爱姑对公共舆论的控制在第二个场景中瞬间失效进而遭遇人生悲剧,是其与制度、人心以及权谋全面对抗后的必然结局。这点可从三个层面考察。一是阶级之别。在迈进慰老爷家大门时,最先出现的是地位至少不如爱姑的众船夫与长年,可“爱姑不敢看他们”。这源于慰老爷家中人多势众的威严感,是伙计们的主子慰老爷及未出场的七大人威慑力的外露。在稍后的叙述中,小说不断强化爱姑明晰的自我阶级定位,并处处流露出自惭形秽与自愧不如的弱者心态,此类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根本差别确乎无法克服。稍后,七大人以知晓新的法权体系的城中大人物身份出场[8],身体健康、衣着光鲜、满面油光的众帮凶们对七大人的维护更给予爱姑以重压,连极其荒唐的把玩“屁塞”行为都受一个群体呼拥。把玩“屁塞”是一个群体精神劣化的写照,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无条件无底线的合谋,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奴化权力结构的生动写照,此番拥护强化了七大人威权之威。所以爱姑此时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七大人,而是一个威权显赫的阶级。二是父亲庄木三的含混态度。吴组缃先生认为庄木三参与爱姑离婚事件有三大好处:“显示自己的威势”“维护自己的体面”“为了要更多赔贴的钱”[9]。前已述及,庄木三带领六个儿子打砸施家是为了洗刷耻辱,可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庄木三疲态多显而有意尽快了结此事,尽可能多拿点补偿,所以打官司和拼命的想法只是爱姑的一厢情愿。此次庄木三携带红绿帖而非六个儿子前来,原因在于庄木三的调解预期,适逢七大人做主为爱姑方多争取了十块钱的补偿后望向庄木三而速获允肯,爱姑也在迟疑中明白了父亲的真实想法,方“觉得事情有些危急了”。至此,爱姑即孤身一人与一个集团抗争,坚持出恶气的诉求已不可能实现。三是爱姑的抗争依据只是必要条件。如陈述自己十五岁嫁入施家后的付出及并不太严重的家暴:“我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从十五岁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10]这些举例欠缺说服力,施家和爱姑的家庭一样并非小康,诸多大小事务需亲力亲为,女性有所疏失而挨打受骂在男权时代并不鲜见。此处的省略号或意味着爱姑认为自己所受苦难之多,或更暗示此类苦难只是一般家庭对待女性的惯常之道,真要抖出几件苦大仇深的冤屈来并非易事。如稍后的勇敢倾诉也仅限于一般日常闹剧:“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鸡,那里是我没有关好吗?那是那只杀头癞皮狗偷吃糠拌饭,拱开了鸡橱门。那‘小畜生’不分青红皂白,就夹脸一嘴巴……”[11]省略号在停顿之外凸显无证可举的窘迫。所以爱姑接下来选择升级自身遭受冤屈的程度,即痛斥丈夫道德败坏而“着了那滥婊子的迷”。当然,此类污名化的道德审判本不合乎事实,爱姑于是直接抬出自己明媒正娶的身份。饶是如此,爱姑发现还是无法撼动威权体系,无法争取到七大人替自己做主。于是爱姑以自己仅有的想象,陈述日后外出打官司和拼命的可能以对抗七大人而显得闹剧感十足。七大人此时甫一开口,所言处处封死爱姑的想象:
“那倒不是拼命的事,”七大人这才慢慢地说了。“年纪青青。一个人总要和气些:‘和气生财’。对不对?我一添就是十块,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于是转脸向着一个尖下巴的少爷道,“对不对?”[12]
这段话有两层内涵。一是七大人顺延慰老爷的和平离婚主张,为爱姑多争取了十块钱的赔偿本为息事宁人,“和气生财”一词满带反讽与戏谑感:七大人发现庄木三如此爱钱,那就多给你一点打发了就好。二是爱姑外出打官司的想象彰显了她对以慰老爷、七大人为代表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质疑与反抗,七大人利用不断强化的威权否决了爱姑的抗争,阻滞了辛亥革命以来乡村社会治理走向现代法治的可能。爱姑此时决定放手一搏做最后抗争,其慌不择言而近乎泼妇骂街,“钻狗洞,巴结人”的恶语相向与夫家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爱姑的行为加重了闹剧因素,甚至具备一点轻喜剧特征。七大人于此只需稍施伎俩,以欺诈手段鼓动威严就可轻易地降服爱姑。爱姑的轻易妥协连慰老爷都表示不快,慰老爷所言“七大人也真公平”的讽刺显然针对的是爱姑对权力的畏惧,当然慰老爷也明显缺乏管理乡村新的公共危机所需要的法权裁断能力。当庄木三迫不及待地想要了结此事,听从慰老爷要求快速拿出“红绿贴”认真清点赔偿金后,这个大厅里的所有人都轻松了:“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紧着的脸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13]于是,一个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形象趋于丰满,这出戏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的范本。历史地看,爱姑所遭遇的封建地主治理体系仍拥有巨大生命力,并未像一般新文学作家所率言已至垂死之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这个体系等同于维护乡村基本结构的稳定。
鲁迅深刻地发现,中国乡村封建治理体系在辛亥革命以来现代法理渗入后有逐渐松动的迹象,然而以七大人为代表的城镇新型士绅势力介入乡村治理后,就切断了这一现代转型的路途,鲁迅再现了辛亥革命以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艰难行进。所以,这是一次由乡民简单的婚事之争久而未决引起的现代乡村治理危机,即“爱姑的反抗动摇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如何处理这个危机是村镇士绅阶级面临的一道新难题。以慰老爷为代表的一批旧有乡村士绅仅仅依靠传统乡村宗法治理的合理性以简单劝和,已经无法弹压如爱姑这类具备一点新见识和相当胆量的不听劝者。因此,只有延请到以七大人为代表的知晓现代城镇法权体系的人物时,这类乡民公共事件才可就地解决,具体解决则是利用现代法权行欺诈与故弄玄虚之实,“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斗争手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些变化”[14]。当然,七大人不能代言现代法治,这也是《离婚》不惜笔墨叙写七大人毫不避讳地恋玩“屁塞”事件的象征与反讽意义所在。七大人的行径如此荒唐而鲜有质疑,原因在于此类爱好在七大人的阶层有普遍性,所谓以玉器“新坑”“老坑”之别证明七大人的“屁塞”品质更出色[15],这是炫耀其资本的表现。七大人于爱姑离婚事件中呈现出的封建性、堕落性与荒谬性是根本性的,这也是鲁迅对辛亥革命以来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的反讽性观察。
(三)危机的平复与秩序的恢复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出由闹剧到轻喜剧再到悲剧的呈现并未就此结束。在文末庄木三与爱姑离开慰老爷家的时候,爱姑居然也轻易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瞬间变得心气平和与温顺大方起来:
“谢谢慰老爷。我们不喝了。我们还有事情……。”庄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说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唔?怎么?不喝一点去呢?”慰老爷还注视着走在最后的爱姑,说。
“是的,不喝了。谢谢慰老爷。”[16]
这才是《离婚》的大悲剧处。在离婚事件的解决过程中,施家顺利纳到小寡妇,成功赶走了形貌不佳又甚为泼悍的爱姑。庄木三在旷日持久的打斗过程中维护了自己的能人尊严,且获得了一定补偿。只有爱姑此刻变得一无所有,成为整个木莲河地区的多余人,日后势必成为一干庸众茶余饭后的笑料。可以推测的是,爱姑必然面临再嫁命运,脾气远大于而能力远不及祥林嫂的爱姑的未来令人担忧。
当然,理性的离婚也应该视作一件和谐的事情。两个人包括双方家庭在内的所有成员从矛盾袭扰中获得解脱,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大限度避免人身伤害,终止并逐渐抚平当事人的心理创伤,这都是应该肯定的。但一次离婚事件,让所有人都成为受益者,只有当事女主人成为最大的牺牲者,是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性的大悲剧处。最为深沉的悲剧在于,当自己成为离婚事件里最大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时,爱姑身处其中而茫然不知,却和众人一起轻松地解脱了,此类表现确为作家对时代女性解放思潮的深刻反讽。当然,该结尾也或许意味着主人公爱姑心灰意懒之后对人生的深刻绝望,神情木讷透露出其对人生命运的刻骨绝望,甚至对未来人生世事的彻骨虚无。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第一个场景中无言无声的两位信佛老太早已勘破世事,直到此时才有了回响,爱姑终于不再执念于申诉而学会了放下,也轻易地陷入深沉的虚无与绝望中了。鲁迅的这种貌似封闭实则开放的结尾设计从事实上留给后来者关于人性与人生的无尽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