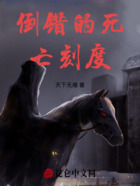
第10章 “展柜里的女人”
祁墨站在警戒线内,目光落在展柜中的女人身上。
法医陈明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声音有些发紧:“死亡时间大约在昨晚11点到凌晨1点,但最奇怪的不是这个。“
她像一件艺术品般被陈列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身穿白色长裙,双手交叠于腹部,面容安详得仿佛只是睡着了。但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苍白,像是被特殊处理过,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的眼睛是睁着的,瞳孔表面覆盖着一层透明的薄膜,在灯光下反射出诡异的光泽。
“她的血液被抽干了,“陈明指着女人手腕内侧的两个细小针孔,“然后注入了某种防腐剂。我们初步检测出甲醛、甘油和一种未知的有机化合物。“
沈昭蹲下身,仔细观察展柜的锁具:“没有被撬的痕迹,凶手有钥匙,或者知道密码。“她的指尖轻轻擦过玻璃边缘,“这里有一道划痕,像是被某种利器刮过。“
祁墨环顾四周。这是市自然博物馆的“极地生物“展区,四周陈列着企鹅、海豹的标本,而此刻,一个人类女性成了其中最“完美“的展品。
“身份确认了吗?“他问。
沈昭翻开平板:“林晚,28岁,博物馆的标本制作师,专门负责海洋生物标本。同事说她昨天下午6点下班后就失踪了。“
祁墨的目光停留在林晚的颈部——那里有一条几乎不可见的细线,像是被极锋利的手术刀划过。
“凶手很专业,“他低声说,“这种切口,只有解剖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做到如此整齐。“
沈昭突然指向林晚的左手:“看她的无名指。“
戒指不见了,但皮肤上留下一圈明显的白痕——戴过婚戒的痕迹。
“查她的婚姻状况,“祁墨说,“还有,调取博物馆最近三个月的监控,特别是林晚工作区域的。“
就在这时,技术员小林急匆匆地跑来:“祁队!我们在展柜底部发现了这个!“
他递过一个密封袋,里面是一片透明的、指甲大小的玻璃片,边缘异常锋利。
沈昭接过袋子,对着灯光观察:“这不是普通玻璃...是载玻片,显微镜用的。“
玻璃片上用极细的笔迹写着一行字:
“第一个标本,完美度70%。“
---
林晚的公寓整洁得近乎刻板。
祁墨戴上手套,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十几个小瓶子,标签上写着日期和拉丁学名。
“福尔马林浸泡的海洋生物标本,“沈昭拿起一个装着小型章鱼的瓶子,“都是她自己制作的。“
书架上摆满了专业书籍:《标本制作艺术》《解剖学图解》《防腐技术史》...祁墨的目光被一本相册吸引。翻开后,他发现所有夫妻合影中,丈夫的脸都被黑笔涂掉了。
“婚姻不和谐?“沈昭凑过来看。
祁墨摇头:“如果是离婚,通常会撕掉或取走照片,不会这样刻意涂抹。“他指着照片角落的日期,“这些都是一年前拍的,之后就没有合影了。“
沈昭的手机突然响起。她接听后,脸色变得凝重:“查到了,林晚的丈夫叫周瑾,是医科大学解剖学副教授,但...一年前就失踪了。“
“失踪?“
“官方记录是登山意外,但尸体一直没找到。“沈昭快速滑动屏幕,“有意思的是,周瑾的研究方向是——人体组织保存技术。“
祁墨的视线重新落回那些被涂黑的照片。一个可怕的猜想在他脑海中成形。
“查一下周瑾失踪案的原始档案,“他说,“特别是他最后出现的地点。“
沈昭点头,突然指向书桌:“那台显微镜有点奇怪。“
显微镜看起来很高端,但底座似乎被改装过。祁墨小心地打开电源,目镜中立刻投射出一段视频: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被绑在椅子上,背景是某种实验室。
视频只有十秒,最后定格在男人惊恐的脸上——和周瑾教师证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视频角落显示着日期:**昨天**。
“他没死,“沈昭倒吸一口冷气,“而且凶手在向我们示威。“
祁墨的目光扫过显微镜的载物台,那里散落着几片用过的载玻片。他拿起一片对着光,看到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第二个标本,完美度会更高。“
法医实验室里,陈明将林晚的尸检报告递给祁墨:“我们在她血液残留物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物质——南极深海鱼体内提取的糖蛋白,能有效防止冰晶形成。“
“这种物质常见吗?“沈昭问。
“极其罕见,“陈明推了推眼镜,“全球只有三个实验室在研究它的医学应用,其中一个就在我们市的医科大学——周瑾负责的项目。“
祁墨的手机突然震动。法证科发来消息:显微镜上的视频经过分析,背景声音中有一段被降噪处理过的旋律。
他点开音频文件,一阵扭曲的钢琴声传来,像是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但节奏明显不对。
“这是...“沈昭皱眉,“倒放的!“
技术科很快还原了原曲——是一首儿歌《十个印第安小人》。
“数字游戏?“祁墨思索着,“第一个标本,第二个标本...凶手在计数?“
沈昭突然站起来:“周瑾失踪前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哪里?“
“北郊的蓝山,“祁墨查看着资料,“当时他声称去采集某种苔藓样本...“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想到了什么。
“蓝山有个废弃的生物研究所,“沈昭快速收拾东西,“上世纪90年代专门研究极地生物标本!“
警车呼啸着驶向北郊。路上,祁墨接到了更令人不安的消息:医科大报告,解剖实验室丢失了一套专业器械,包括骨锯、解剖刀和一套血管灌注设备。
“他不是在杀人,“祁墨握紧方向盘,“他是在收集标本。“
当车停在废弃研究所前时,天已经黑了。建筑像一只蹲伏的野兽,黑洞洞的窗口如同眼睛注视着他们。
沈昭拔出手枪:“我觉得他在等我们。“
祁墨无声地点点头,推开了生锈的铁门。
门内,走廊两侧摆满了玻璃罐,福尔马林液体中漂浮着各种器官标本。最尽头的大门上,用鲜血写着:
“欢迎参观我的画廊,警官们。“
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像有形之物般缠绕在鼻腔里。祁墨推开尽头的金属门,手电筒光束刺破黑暗,照亮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场景——
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内,十二个透明玻璃罐整齐排列在铁架上。每个罐子里都悬浮着人体器官:心脏、肺叶、眼球...所有器官都被处理得异常完美,血管中注射了彩色防腐剂,在灯光下呈现出诡异的艺术感。
“上帝啊...“沈昭的呼吸明显加速,“这些都是...“
“周瑾的作品。“祁墨的手电光照向墙面。那里钉着十几张解剖图纸,每张都标注着日期和精确到0.1克的防腐剂配方。最新的一张图纸上写着:“最终阶段:完整人体保存(目标存活时间72小时)“
沈昭突然抓住祁墨的手臂。她的指尖冰凉,指向角落里的监控屏幕。屏幕突然亮起,显示出一个实时画面:手术台上躺着昏迷的周瑾,他的胸腔已被打开,但心脏仍在跳动。仪器显示体温降至22℃,呼吸频率仅为正常值的30%。
“低温休眠状态...“祁墨的喉结滚动,“他在拿活人做实验。“
屏幕下方闪烁着一行倒计时:06:23:15
沈昭迅速联系技术科:“追踪这个视频信号!“她的声音在空旷的实验室里回荡。
祁墨走向房间中央的操作台。显微镜下固定着一张载玻片,上面排列着六个完美切割的人体组织切片,排列成雪花形状。旁边的手写笔记记载着:
“第七次尝试终于突破冰晶难题。关键在于海参糖蛋白与南极地衣素的23:7配比。L的皮肤保存度达到92%,但肌肉组织仍有收缩...“
笔记突然中断,最后一行写着:“需要新鲜样本验证。“
操作台抽屉里放着一本皮质相册。沈昭翻开后倒吸一口冷气——里面是林晚工作时的偷拍照,每张照片都标注着她处理标本的步骤细节。最后几页则是周瑾在医科大学授课的照片,其中一张被红笔圈出:他正在演示心脏灌注技术。
“不是复仇...“沈昭的声音发紧,“是'技艺传承'。“
祁墨的手机突然震动。技术科发来定位结果:信号源在博物馆地下二层标本储藏室。
两人冲出研究所时,暴雨倾盆而下。警笛划破夜空,但祁墨知道,他们正在踏入凶手精心设计的标本盒——每一步都在对方的实验记录之中。
市博物馆地下二层的温度比上面低了至少十度。沈昭的枪口随着手电光束移动,照亮走廊两侧的标本柜。浸泡在防腐液中的海洋生物用空洞的眼睛注视着不速之客。
“温度监测显示最冷点在尽头房间,“祁墨查看手机上的建筑平面图,“原先是极地标本专用储藏室。“
他们停在厚重的金属门前。门缝里渗出丝丝白雾,门把手上结着薄霜。祁墨试着推了推——门被从内部锁死了。
沈昭发现门禁键盘上有几个按键磨损严重:“密码可能是四位组合,2、3、7、9使用频率最高。“
祁墨尝试了周瑾工号尾数2379。门锁发出“滴“的一声,红灯转绿。
“他想要我们进来。“沈昭轻声说。
推开门的那一刻,冷雾扑面而来。房间中央的透明低温舱如同水晶棺材,周瑾就躺在里面,胸口的手术切口被暂时缝合,身上连接着各种监测仪器。舱体显示内部温度-25℃,而他的生命体征微弱但平稳。
“他还活着!“沈昭冲向控制台,“需要立即升温...“
“别动!“祁墨厉声制止。他的手电光照向舱体底部——四条输液管连接着不同颜色的液体罐,全部汇聚到一个精巧的平衡装置上。任何不当操作都会导致装置倾斜,切断生命支持系统。
墙上投影仪突然自动开启。画面中是周瑾的影像,他的声音经过变声处理:
“祁警官,沈警官,欢迎来到最终展厅。如果你们看到这段录像,说明我的计算完全正确——包括你们破解密码的时间。“
画面切换成实验室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周瑾给自己注射了某种药剂,然后有条不紊地切开自己的胸腔,将防腐剂导管插入心脏。整个过程没有助手,但他的每个动作都精准得可怕。
“人体自我保存实验,终极阶段。“录音继续播放,“当核心体温降至20℃时,细胞活动将减缓至千分之一。理论上,一个人可以这样保存自己...直到被唤醒。“
沈昭正在悄悄联系救援队,突然发现控制台下方贴着一张便签:
“升温速率不得超过0.5℃/小时,否则蛋白质会——“
后面的字被血迹模糊了。
祁墨检查低温舱周围,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小型冷藏箱。里面整齐排列着七个玻璃瓶,每个瓶子里都漂浮着不同的人体组织切片。最后一个瓶子是空的,标签上写着:“第七阶段:神经丛保存(待完成)“
瓶底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周瑾和林晚站在医学院门口,两人中间是第三个人——一个左眼戴着黑色眼罩的老者。照片背面写着:“导师说,真正的标本应该永远微笑。“
救援队赶到时,技术专家也被眼前的装置震惊了。“这简直是科学怪人的作品,“首席医学生理学家检查后说,“他用南极鱼抗冻蛋白改造了自己的血液,理论上确实可以...“
“能救活吗?“沈昭打断他。
“如果严格按照他的方案...“专家擦了擦汗,“但需要他本人留下的解冻程序。“
祁墨的目光落在墙角的标本柜上。那里多了一个之前没注意的玻璃罐,里面漂浮着一张完整的人脸皮肤——正是照片中独眼老者的面容,嘴角被缝合出诡异的微笑。
罐体标签写着:“第一个完美标本,致我最敬爱的导师。“
三天后的特护病房里,周瑾的心电图终于趋于稳定。他的体温被严格控制在34℃,足够维持生命又不至于加速组织代谢。警方在病房外布置了严密看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案子远比表面复杂。
“他导师的档案查到了,“沈昭递给祁墨一份文件,“维尔纳·克劳斯,德裔标本学家,二十年前在极地考察时发生事故,左眼失明。官方记录显示他五年前死于癌症,但...“
“但尸体不见了。“祁墨接话,翻看验尸照片。照片上的老人躺在停尸房,右眼圆睁,左眼的黑色眼罩依然戴着。
法医陈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检测报告:“你们得看看这个。周瑾血液里的抗冻蛋白序列...与博物馆死者林晚体内的完全一致。“
“他用自己的妻子做实验?“沈昭难以置信。
“不,“祁墨突然明白过来,“是共同研究。那些笔记上的'L'不是指林晚的姓氏,而是'Love'的缩写。“
他调出林晚电脑里加密文件夹的最后视频。画面中,林晚穿着白大褂站在低温舱前,声音冷静得可怕:
“第七阶段实验日志。我们终于破解了神经冷冻损伤难题。按照计算,人体可以在-25℃环境下保存至少120年。明晚将进行最终测试,志愿者是我自己。“
视频戛然而止,日期显示是案发前一天。
病房里的监测仪突然发出尖锐警报。周瑾的眼皮剧烈颤动,在所有人反应过来前,他的眼睛猛地睁开——那双眼球呈现出不自然的玻璃质感,在灯光下反射出标本般的光泽。
他的嘴唇蠕动着,祁墨俯身去听。
“她...成功了...“周瑾的声音像是从冰层深处传来,“我们...都会...微笑...“
当警员们冲进病房时,周瑾的心电图已经变成一条直线。他的嘴角被某种内部机制牵动,缓缓扬起一个标准到毫米的微笑——与玻璃罐里漂浮的导师面孔如出一辙。
结案报告会上,技术科展示了对周瑾工作室的最终发现:七个冷藏箱分别标记着“阶段1“到“阶段7“,最后一个箱子里整齐码放着二十三支装有透明液体的安瓿瓶,标签上写着:
“永生之酒——致未来发现者。“
沈昭合上档案夹时,发现底部粘着一张之前没注意的载玻片。对着光能看到上面刻着极小的字:
“第八个标本将是完美的。你们准备好了吗?“
窗外,暮色中的博物馆灯火通明。新一期的特展海报在夜风中轻轻摆动,上面写着《永恒的瞬间:人体艺术展》。海报角落,一个戴眼罩的老者肖像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