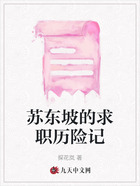
第3章 杏坛起微澜,剧本杀难敌签到表
直播带货此路不通,苏子瞻痛定思痛。
想他苏轼,好歹也是进士出身,宦海沉浮之余,诗词文赋,传颂千年,教书育人,总该是自己的本行吧?
当年在黄州,尚能聚徒讲学,何况如今这文教昌盛之地?
他打定主意,要去这杭州城里最高的学府——浙江大学,谋个教席。
然而,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当他拄着竹杖,找到浙大某个学院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接待他的那位年轻行政老师,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他,然后公式化地回答:“对不起,先生,我们招聘教师,首先需要博士学位,其次必须持有国家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请问您有吗?”
苏子瞻哪有什么“博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
他空有满腹经纶,却连大学的门槛都摸不到。
正当他准备失望离去时,一位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教授恰好经过,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老教授似乎对苏子瞻的穿着和谈吐很感兴趣,主动上前攀谈。
几番交流下来,老教授被苏子瞻那渊博的学识、豁达的谈吐以及对宋代文史信手拈来的熟稔所深深折服,惊为天人。
这位老教授在历史系颇有威望,在他的极力引荐和担保下,苏子瞻破格获得了面见校长的机会。
校长办公室里,面对这位谈吐间引经据典、气度不凡的“奇人”,校长也感到十分惊讶。
虽然对其“穿越”的说法持保留态度,但爱才之心油然而生。
最终,校长决定冒险一试,特批他开设一门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不占编制,按课时发放劳务费。
课程名称,就定为《宋词里的烟火人间》。
苏子瞻终于站上了阔别千年的讲台,虽然这讲台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下面坐着的学生们穿着各异,人手一个“小方块”。
他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
第一堂课,他没有用PPT(他也不会用),也没有照本宣科。
他决定来点不一样的。
他将课堂“搬”到了户外,带学生们来到烟波浩渺的西湖边,指着潋滟的湖光山色,现场吟诵并讲解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他告诉学生们,诗词不仅在书本里,更在山水间,在生活中。
此情此景,若能配上一杯新沏的龙井,或是一块刚出炉的荷花酥,那便是“色香味”俱全的体验了。
学生们听得入了迷,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发“朋友圈”。
一时间,西湖边这小小的一角,充满了诗情画意。
然而,好景不长,校园保安骑着电动巡逻车赶了过来,用高音喇叭喊话:“干什么的?这里不允许搞聚集性活动!影响校园秩序!请立刻解散!”
苏子瞻据理力争:“吾乃浙大教师,此为课堂教学……”
保安不为所动:“有审批手续吗?没有审批就是非法聚集!赶紧散了,不然我们要上报了!”
最终,这场别开生面的“现场教学”只能在保安的催促下草草收场。
苏子瞻望着被驱散的学生,无奈地摇摇头,心中暗忖:昔日吾为杭州太守时,亦未曾见西湖有此等森严规矩。
回到课堂,他尝试用更“现代”的方式吸引学生。
他发现学生们似乎很喜欢一种叫做“剧本杀”的游戏,便灵机一动,设计了一套“宋词剧本杀”。
他选取了自己那首著名的《蝶恋花·春景》为蓝本:“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让学生们分别扮演词中的“墙里佳人”和“墙外行人”,通过搜集线索(词句意象)、完成任务(对诗、填词),来体验那份“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微妙情愫。
这下课堂气氛果然活跃了许多,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对宋词的理解也似乎更深了。
苏子瞻颇为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古今结合的好方法。
然而,麻烦也随之而来。
不久之后,他被学院的学术委员会约谈。
几位表情严肃的教授告诉他,有学生和家长反映,他的教学方式“过于娱乐化”,担心会“消解经典的严肃性”,建议他回归传统的讲授模式。
他申请用于开发更多“剧本杀”道具和资料的经费,自然也被冻结了。
在教学评估会上,教务处的负责人拿着一叠表格,对他的课程提出了“改进建议”:“苏老师,您的课学生评价比较两极化。优点是生动有趣,互动性强。缺点也比较突出,主要是缺乏量化的考核标准,课堂管理不够规范。我们建议您引入课堂签到系统,使用标准化的PPT课件,增加随堂测验,期末考试最好采用客观题为主的形式,比如选择题、填空题,便于统一评分。”
苏子瞻听得瞠目结舌。
他一生治学,讲究随心而发,师生问答,重在启发,何曾需要什么“签到”、“量化”、“客观题”?
他试图解释自己的教学理念,但面对着那些冰冷的表格和术语,他感到自己的话语是如此苍白无力。
他鼓励学生自由思考,抒发真情实感。
期中考试,他不设具体题目,只要求学生“就本学期所学,择一感触最深之处,文体不限,有感而发,随心而著。”
他期待能看到学生们灵光闪现的篇章。
结果收上来的作业五花八门,有写得情真意切的读后感,也有格式工整但内容空洞的“论文”,甚至还有一篇让他哭笑不得的“商业计划书”,题目是《论苏轼个人IP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变现可能性研究与路径探索》,里面还像模像样地分析了他的“粉丝画像”、“商业价值”和“可开发周边”。
更让他郁闷的是,他偶然看到一位历史系研究生发表的论文,题目是《苏轼美食思想的当代应用与商业转化研究》,里面引述他的诗词和观点时,出现了多处明显的错误和曲解。
他出于文人的较真和对后学的责任感,忍不住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勘误信,寄给了发表该论文的学术期刊编辑部。
没过几天,他收到了编辑部的邮件回复,内容简洁而冰冷:“尊敬的苏子瞻先生,经核实,您的观点与主流学术界存在较大差异,且近期多次发送类似邮件,已对本刊正常工作造成干扰。为免误会,您的邮箱已被系统自动列入黑名单。感谢您的关注。”
苏子瞻看着那封“拉黑”邮件,气得手都发抖了。
想他苏东坡,何曾受过这等待遇!这世道,真是……不可理喻!
期末,由于他坚持不搞标准化考试,不强制签到,最终被几位“追求绩点”的学生投诉到了教务处,定性为“教学事故”。
虽然老教授出面斡旋,勉强保住了他的选修课,但他已经心灰意冷。
这里的条条框框,比大宋的官场还要令人窒息。
他站在未名湖……哦不,是浙大某个不知名的小池塘边,看着水面倒映出的自己落寞的身影,长叹一声:“此间非吾自在处,不如归去……且归去卖饭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