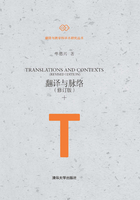
二、“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
英文的“translate”来自拉丁文的“translatus”,意指“转移、迁移、搬动、传递”,强调的是空间的面向和越界的行动,仿佛具体的对象被带着跨越语言、文化、国族的疆界,而在另一个语言、文化、国族的脉络中落地生根,成长繁衍。梵文的“anuvad”意指:“在……之后说或再说,借由解释而重复,以确证或实例来做解释性的重复或反复,以解释的方式来指涉已经说过的任何事”(“saying after or again, repeating by way of explanation, explanatory repetition or reiteration with corroboration or illustration, explanatory reference to anything already said.”[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9])。此处着重的是时间的面向(尤其是“延迟”“后到”[belatedness])和解释、重复之意。 中国自周朝起便有关于翻译的文献记载,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戴圣,1965:11)因此,“译”原指专事北方之通译。许慎(1965:22)《说文解字》把“译”扩大解释为“传译四夷之言者”。类似的说法除了明指“语言的传达”之外,更暗示了我们/他们,中心/边缘(中土与四方),文明/野蛮(华夏与蛮夷)之辨。由“translatus”“anuvad”与“译”的含义,可以看出其中涉及空间性、时间性、分野、阶序与高下。那么居中的译者之地位与角色又如何呢?
中国自周朝起便有关于翻译的文献记载,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戴圣,1965:11)因此,“译”原指专事北方之通译。许慎(1965:22)《说文解字》把“译”扩大解释为“传译四夷之言者”。类似的说法除了明指“语言的传达”之外,更暗示了我们/他们,中心/边缘(中土与四方),文明/野蛮(华夏与蛮夷)之辨。由“translatus”“anuvad”与“译”的含义,可以看出其中涉及空间性、时间性、分野、阶序与高下。那么居中的译者之地位与角色又如何呢?
以往对译者的看法偏向于消极、负面、被动。一般的说法是,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服侍着两位个性迥异、要求不同的主人(serving two masters),因此往往陷入左支右绌、动辄得咎的窘境。而译者经常被称为在从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a thankless job):优点与荣耀尽归于作者,缺失与遗憾则全属于译者;译文的措辞与句法若太像原文,虽有可能被赞为忠实,但更可能被说成生硬不通、食“外”不化的直译、硬译甚至死译;反之,译文若太像标的语言(target language)般流畅通顺,则又可能被质疑为了迁就本国语言而牺牲了原文的特色以及失去了可能丰富标的语言的机会。 总之,翻译若“过”,则犯了“添加之罪”(sin of commission),若“不及”则犯了“省略之罪”(sin of omission)。更糟的是,“过”与“不及”的定义和标准不但人言言殊,而且可从原文(译出语)与译文(译入语)的双重角度来检视。因此,译者就成了语言夹缝间动辄得咎的中间人,沦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对象,而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或“译者,逆者也”)这种怀疑、敌视、贬斥的说法,也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若是译文平顺或表现平平,乏善或乏“恶”可陈,则又仿如透明的载具,读者透过译文直取文意,以致“得意忘言(译文)”的同时,也忘了译者的存在。换言之,译者的宿命似乎不是被斥为“过”或“不及”(有时“两罪并发”)的违逆者,就是沦为无人闻问、视而不见的透明人——而后者正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痛斥的。
总之,翻译若“过”,则犯了“添加之罪”(sin of commission),若“不及”则犯了“省略之罪”(sin of omission)。更糟的是,“过”与“不及”的定义和标准不但人言言殊,而且可从原文(译出语)与译文(译入语)的双重角度来检视。因此,译者就成了语言夹缝间动辄得咎的中间人,沦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对象,而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或“译者,逆者也”)这种怀疑、敌视、贬斥的说法,也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若是译文平顺或表现平平,乏善或乏“恶”可陈,则又仿如透明的载具,读者透过译文直取文意,以致“得意忘言(译文)”的同时,也忘了译者的存在。换言之,译者的宿命似乎不是被斥为“过”或“不及”(有时“两罪并发”)的违逆者,就是沦为无人闻问、视而不见的透明人——而后者正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痛斥的。
然而,译者的地位果真如此不堪?在巴别塔之后,语言遭到错乱、无法直接沟通的世人,势必要仰赖译者;而“拈花微笑”“不立文字”“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说法,就是因为稀罕,才会广为传诵,引为美谈。如果说巴别塔之后,翻译是“必要之恶”,那么即使是恶,仍属必要。 因此,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根据自身翻译的实务经验指出,若只是一味质疑、批判翻译,要等待完美的译者出现才从事翻译,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因此,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根据自身翻译的实务经验指出,若只是一味质疑、批判翻译,要等待完美的译者出现才从事翻译,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斯皮瓦克说:“只是批判,延缓行动一直到产生乌托邦式的译者之后,是不切实际的。”(“To be only critical,to defer action until the production of the utopian translator, is impractical.”[Spivak, 1993:182])斯坦纳(George Steiner)直截了当地指出:“因为翻译并不总是可能,而且从未完美,就否认翻译的有效性,这是荒谬的。”(“To dismiss the validity of translation because it is not always possible and never perfect is absurd.”[Steiner, 1998:264])翻译家庞提耶若(Giovanni Pontiero)则采取更积极、正面的态度予以响应:“如果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绝对之事,那么它就是一件值得努力的绝对之事。”(“If the perfect translation is an impossible absolute, it is an absolute worth striving for.”[Pontiero, 1997:26])一般说来,似乎理论家比较倾向于强调不可译性,而译者虽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遭逢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比一般人有着更深切的体会,但基本上采取“先译再说”“且译且走”,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0A3F34/154776438045424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51573-tBo8QhpioxpsCPIuHZ8jWtsW4XAMZgaj-0-b88323267b4232ef829f0ec12cb75eac) 更何况对巴别塔之后的世人而言,除非不与异语者来往,否则早已置身于翻译之中了,而后来者更“总是已经被翻译了”(always already translated)。
更何况对巴别塔之后的世人而言,除非不与异语者来往,否则早已置身于翻译之中了,而后来者更“总是已经被翻译了”(always already translated)。 因此,与其依循旧绪,以消极、负面、被动的方式来贬抑这件必要之事,不如改弦易辙,以积极、正面、主动的方式来观察此一现象,并从生产的(productive)与践行的(performative)角度来看待译者。换言之,“翻译”与“译者”在当今的时空脉络下亟须重新诠释与翻译,以争回(reclaim)应有的地位;而类似“翻译者,反逆者也”的说法或“中伤”,也需进一步加以“翻译”与“反逆”。
因此,与其依循旧绪,以消极、负面、被动的方式来贬抑这件必要之事,不如改弦易辙,以积极、正面、主动的方式来观察此一现象,并从生产的(productive)与践行的(performative)角度来看待译者。换言之,“翻译”与“译者”在当今的时空脉络下亟须重新诠释与翻译,以争回(reclaim)应有的地位;而类似“翻译者,反逆者也”的说法或“中伤”,也需进一步加以“翻译”与“反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