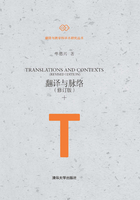
三、译者的翻转/翻身
相关的挑战与反逆可由两个角度来探讨。从欧美的思潮来观察,其中荦荦大者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著名的三个比喻——碎瓶、切线、来生——来讨论翻译,既颠覆了原文作为源头的权威,也质疑了译文与原文如影随形的关系,试图为译文缔造新生。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进一步发挥,消解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主从、甚至主奴关系,而拈出“互补”(complementarity)之说。 至于德·曼(Paul de Man)的理念与实作之间的落差也值得观察。他以本雅明的理论及其英译为例,主张不可译性,但在证明其论点时,却以另一人的佳译和自己的英译来质疑先前英译之不妥,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明显可见。
至于德·曼(Paul de Man)的理念与实作之间的落差也值得观察。他以本雅明的理论及其英译为例,主张不可译性,但在证明其论点时,却以另一人的佳译和自己的英译来质疑先前英译之不妥,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明显可见。
另一方面是从后殖民论述的角度切入。在理论方面如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特重翻译之情境与脉络,以历史化的思维重新省视翻译,尤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将翻译视为反抗与转化的场域。巴巴(Homi K. Bhabha)有关文化翻译的说法以及拟态(mimicry)等观念,也为被殖民者的抵抗、反扑、逆写提供了理论根据。而斯皮瓦克身兼理论家与翻译者的双重角色,由早年从法文英译德里达的《书写学》(Of Grammatology)并撰写长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到后来挟多年学术声望,英译故乡孟加拉女作家戴薇(Mahasweta Devi)的《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 Three Stories by Mahasweta Devi),附上访谈、序言、译注、跋语,将她推上国际文坛。她的翻译实践与具体、平实、可行的翻译观,足堪借鉴。这两股思潮合流,大大挑战了旧有的翻译观,也为译者的翻转/翻身提供了契机。
如果我们从“翻译”开始反逆,那么“Traduttore,traditore”在“翻译成如此丰富、如此不同于英文(就此处而言,意大利文)、如此具有光辉的文学传统和知识传统的中文”之后(米勒,1991:8),衍异/演义出繁复纷杂的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就“翻译者,反逆者也”或“译者,逆者也”这个中文翻译而言,至少具有三重意义:违逆、追溯、预测。其中,“违逆”“不肖”(后者取其“不像”与“恶劣”二意),最贴近意大利文原意和当今的中文用法。“追溯”则取“以意逆志”之意, 虽然难免“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之讥,却也是人类理解(human understanding)以及读书—知人—论世的重要方式。“预测”则取“逆睹”“逆料”之意,把目标投射于未来——虽然这种预测可能违逆/ 违反原来的意思,以致有“不肖”之讥。如此说来,译者有意无意之间集三重意义于一身,综合了逆与顺、反与正、不肖与肖似、前瞻与回顾、开创与溯源。这种说法似乎在米勒强调理论经过翻译之后在异地的新开始之外,
虽然难免“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之讥,却也是人类理解(human understanding)以及读书—知人—论世的重要方式。“预测”则取“逆睹”“逆料”之意,把目标投射于未来——虽然这种预测可能违逆/ 违反原来的意思,以致有“不肖”之讥。如此说来,译者有意无意之间集三重意义于一身,综合了逆与顺、反与正、不肖与肖似、前瞻与回顾、开创与溯源。这种说法似乎在米勒强调理论经过翻译之后在异地的新开始之外, 还同时包含了时空两个面向的越界:既溯源也创新,既回顾也前瞻,“既读取也传送”(“to retrieve and relay”, Hatim & Mason,1997: viii)。而造成这一切的关键人物正是译者。原先动辄得咎、两面不讨好的“译者/逆者”,在“翻译”之后竟能如此的翻转与翻身,真可谓“不可逆睹”。果真如此,又该如何看待译者的角色呢?
还同时包含了时空两个面向的越界:既溯源也创新,既回顾也前瞻,“既读取也传送”(“to retrieve and relay”, Hatim & Mason,1997: viii)。而造成这一切的关键人物正是译者。原先动辄得咎、两面不讨好的“译者/逆者”,在“翻译”之后竟能如此的翻转与翻身,真可谓“不可逆睹”。果真如此,又该如何看待译者的角色呢?
从本文开头所叙述的米勒轶事可以看出,其实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绝非作者宰制译者的单向关系,反而是相当程度地翻转了。正如笔者在《理论之旅行/翻译》一文中所言,“原先为权力/权威来源的原作者,在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中,成为必须仰赖他人(即译者)的能力、善意、用功的被译者”。笔者并指出,“在晚近的翻译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为译者的身份、地位呼吁,强调他们身为再现者/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评论者甚至颠覆者的角色”(本书第195页)。此处拟进一步分述译者的不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