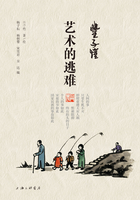
谈抗战歌曲
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戏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艺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我在江西坐船走水路,常夜泊荒村,上岸游览,亲耳所闻),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柳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平易浅明,世人有“老妪能解”之评。现在的抗战歌曲,当然比白居易的诗更为平白,直可称之为“幼童能解”。原来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故我们民间音乐发达,即表明我们民族精神昂奋,是最可喜的现象。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古语云:“大行不顾细谨。”在国家存亡危急的今日,对于艺术不宜过于严格地批评。只要不妨碍抗战精神而具有几分价值的,我们都应该容纳或奖励。让它们多多益善地产生。古语云“曲高和寡”。现在却相反,应说“曲好和众”。因为现在对于艺术不求其“高”(高就是深,在绘画是“气韵生动”的杰作,在音乐是“流水高山”之类的名曲。它们自有其高贵的艺术的价值。这种艺术在近代被称为“为艺术的艺术”,或“象牙塔中的艺术”,只宜让少数优越分子互相欣赏,不宜作为民众艺术),但求其“好”。所谓好,就是有耳共赏。凡不含毒质而合乎大众胃口的,都是好曲。现在抗战歌曲虽如雨后春笋,但到后来自然会淘汰,只剩最好的——就是最合大众胃口而不含毒质的——几曲流行于民间。所以不妨让它们多多益善地产生,不应该作严格的批评。现在写这篇,竭力避免严格的批评,但对抗战歌曲略略贡献一点意见。
关于抗战歌曲,可就三方面而谈:第一是歌词,第二是乐曲,第三是乐谱。
现行的抗战歌曲的歌词,就是抗战文学的一部分,固然慷慨雄壮,没有一曲不是怒发冲冠的喑呜叱咤。但我翻了许多抗战歌曲集,觉得有两点惹我注意:第一是略觉“千篇一律”。譬如“起来,起来”“前进,前进”之类,固然是促醒民众的有力的呼号,但用之太多,反觉疲乏。用之不得其当,反失效力。我以前做教师时,曾有这样的经验:上课时儿童注意力不集中,须得用高呼,或在黑板上拍教鞭,以促其注意,使全体静肃听讲,但倘滥用此法,不住地高呼,不住地拍教鞭,到后来会失去效用。那时就非用别种较软的方法,譬如讲一故事,唱一歌曲。我忽然改变上课的态度,倒可以引起儿童注意,使大家一致团结。抗战歌词,我以为也如此。高呼“起来”“前进”“奋斗”“杀敌”的固然少不得,别种和平奋斗的歌词也应该有。但现在前者很多,而后者很缺。故不免千遍一律。这是第一点。第二,我翻阅了许多抗战歌曲集,觉得歌词的意义,大多数只给人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少有动人的艺术味。换言之,大多数像“标语”的连缀,而不像“歌词”。这些歌曲当然也有效用,但其效用与标语相去无几,或可说是“朗吟的标语”。我觉得这种以外,应该再有含有艺术味的——含有诗趣的——歌词。表面看来并不轰轰烈烈,其实感人之力有时反比前者为大。举一做例,即《心头恨》:
这歌词,在现行许多抗战歌词中,是很难得的一首。(在一本歌集中,恐怕难得找出第二首来。)作者用比喻开始,慢慢地说到抗战。表面上似乎“不雄壮”,“太柔弱”,其实你回味一下子看,反比“朗吟的标语”力强!而我所谓“诗趣”,就是指此。作诗有赋、比、兴三体。大概“比”和“兴”比“赋”更富有诗趣,其入人也更深。但“赋”也可以作成好歌词。只要不一味呼号抽象的概念文句,而加以动人的叙述描写(就是诗趣),也是好歌词。这种好歌词现在一定有。但我手头找不出例子,只得举两首古人词来举一反三。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是大家知道的。其词云:
这首词倘被译成白话,一定是能使大家动听的。动听的原因就在善于叙述描写,而含有诗趣。还有一首,是一位女子作的,也很可以提出来看。这女子是岳阳守土者徐君宝之妻。徐被寇兵所杀,女被劫至杭州,寇欲犯之,女佯诺,但须奠祭先夫然后从。寇许之。女奠毕,题此词于壁,自刎死。词曰:

抬望眼,仰天长啸
此词虽是一女子的委婉的叙述,但读起来一步紧一步,终于令人悲愤填胸,怒发冲冠。此次日寇的暴行之下,我民族的悲壮行为,类乎此者极多。在文学中一定有了动人的描写,但在歌曲中我没有见过。倘得选出或作出这类的歌词来,谱之以曲,流传民间,其声音一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以上是关于歌词方面的。
第二,关于乐曲方面,话很难说。因为我们中国民众的音乐教养,现在还很浅,对于作曲好坏的辨别力很缺乏。过去十年间,大多数的民众,曾经上过一种小歌剧的当。被那种小歌剧的油腔滑调的旋律所蛊惑,中国民众养成了一种爱好淫乐的习惯。所谓淫乐,即古人所谓郑卫之音,就是亡国之音。“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我国抗战以前,自伐的确太多。贪官污吏、国内纠纷的自伐之外,那些亡国之音也是自伐之一种。试听那些小歌剧的旋律,优柔颓废,萎靡不振,能把世间一切东西软化。壮汉听了会变弱女,老虎听了会变花猫,火烧时唱起来火会熄灭的。过去十年间,这种旋律软化了我们中国的民众,招致了莫大的祸殃!但罪不在于民众,而在于作者和书商。因为民众没有充分的音乐教养,全是未染之素丝,教他们好的歌曲,他们就趋向好。教他们坏的歌曲,他们就趋向坏。而好的歌曲,往往不容易感动民众;反之,坏的歌曲,往往极易普遍流行。这犹之行舟,上溯困难,下流全不费力。所以那些不良小歌剧,流行得特别顺利快速,深入于全国的到处。
最近几年来,渐渐有人注意此事。音乐界的志士,群起而攻。于是在都市里,这种音乐渐渐少有听到。(但在无知的乡村中,还在那里取作小学校的音乐教材。)作曲者努力创作勇猛的歌曲,拿来同它们抵抗。这一反动,非常有力。现行的抗战歌曲中,有不少“进行曲风”的作品,慷慨激昂,气焰冲天,唱起来令人联想到军队的进行及冲锋杀敌。这些歌曲,在现今的抗战时期,确有增强军民抗敌情绪的效用。从前拿破仑的兵能开过阿尔卑斯山,据说全靠音乐帮忙的。现今我们抗敌的胜利,恐怕也有赖于这些歌曲。
如上所说,我们的旋律已由柔靡之音反动而为猛勇之曲,诚然是可喜的事。但我对于作曲界还有两个小意见贡献出来:
第一,勇猛之曲以外,必须再有一种“和平奋斗”的音乐。其旋律须“深沉,伟大,雄壮,威而不猛”,以合于我们的“长期抗战”之旨,以表出我们的“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的精神。因为一味勇猛的歌曲,只宜为短期间冲锋杀敌之助,不合于后方长期抗战的鼓励。况且此次抗战,我们的任务不但是杀敌却暴,以力服人而已。我们还须向全世界宣扬正义,唤起全世界爱好和平、拥护人道的国民的响应,合力铲除世界上残暴的非人道的魔鬼,为世界人类建立永远的和平幸福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不可以“好小勇”,不需要“暴虎冯河”的精神,而需要“深沉,伟大,雄壮,威而不猛”的精神。希望作曲者本此精神,多作好曲,实为抗战前途之大利。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我以为现在的作曲,宜取“宣叙风”(recitative)。宣叙风者,就是近于朗诵式的乐曲,浅近地譬喻,就像小贩子们叫卖的调子——不是“说”而是“唱”,但唱的个个字眼都听得清楚。再取一个比喻,好比唱大鼓词——不是“说话”而是“唱戏”,但唱的个个字眼都听得清楚。(反之,像京剧就不然,一个字的尾音曲曲折折地拖得很长,倘不曾看过戏考,无从听出所唱的什么话。)何以要用这种“宣叙风”呢?因为,抗战歌曲务求其普遍于民众,务使全国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兵,以及文盲,都听得懂。听得懂,就有兴味,有兴味就肯唱,大家肯唱,就好。这种曲的作法,第一件要事是必须先有歌词而后作曲。作曲者拿歌词来读熟,朗诵几遍,宣叙风的旋律自然会产生。这原是作曲的正规。[西洋歌曲作家,像Schubert(舒柏特)常手拿一册Goethe(歌德)诗集,在室中漫步朗诵。朗诵到后来,乐曲的旋律忽然在脑中出现,立刻奔到桌子前面去写谱。]那么现在我何必多说呢?因为中国人作歌曲,往往不取这正规的办法,而在曲子上配文词。配文词的人倘是理解音乐的,原也未始不可。他可以先把曲子唱熟,然后依乐句而配相当的文句,也能作成很调和美满的歌曲。但倘配文词的人不理解音乐,由别人在曲子下面圈几个圆圈,规定句子的长短,然后请他在圆圈中填入文字,不管文字与上面的旋律是否相合。这样产生的歌曲,唱起来很不自然。有时乐句很昂奋,而文句却是舒缓的;有时乐句很舒缓,而文句却是昂奋的。唱起来岂不滑稽可笑?故抗战歌曲,最好是先作歌词而后谱曲。万一要倒做,作歌的人必须理解乐曲,熟读乐曲。总之,务使音乐与歌词融合一体。即务使乐曲成为宣叙风的音乐,务使歌词成为朗吟式的文句。现行的抗战歌曲中,这种宣叙风的作曲也有,但比较的少。最常听到的例,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句法。从来没有听到这曲的人,一听到就可知道唱的是这么一句话。这便是宣叙风作曲的特点。反之,初次听到时,只觉得高高低低的许多音带了一群辨不清楚的文字而响着,完全听不出文字所表出的意义,便是非宣叙风的作曲,或竟不成为歌曲。以上是关于乐曲方面的。

战争与音乐

战争与音乐
第三,关于乐谱方面,问题较小。这就是五线谱和简谱的问题。中国人本来不喜看(或不能看)五线谱。自从口琴音乐盛行以来,简谱愈加发达。自从抗战以来,为求普遍化,各种抗战歌集就老实不客气地把五线谱废止,公然地用简谱了。普遍化原是要紧的,但音乐艺术的因陋就简,也是可惜的。书商欲免制锌版,借口“大众化”“普遍化”的名目而排印简谱,不用锌版,书的定价可以较低,读者的负担可以减轻,原也是好事。但我总希望在可能范围内多用五线谱,至少五线谱同简谱并用。因为在这非常时期中因陋就简,深恐将来大家看惯了简谱,从此对于五线谱愈加疏远,中国音乐教育前途将受阻碍。因为简谱只能记载极浅易的乐曲,不能记载较复杂的乐曲。风琴、洋琴(钢琴)弹奏的音乐,简谱就不便记录。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现在我也不多说了。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