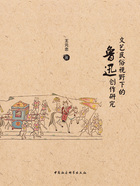
二 新文学的民间化取向
“五四”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的一种构成,对应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向下看”的态度变化,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在价值的建构中显现出了一种鲜明的民间化取向。
这一新的价值取向,不仅标示了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使“五四”新文学显现出了某种区别于古典文学的现代性或新形态,而且也唤醒了新文学参与者们的民间底层意识,促发了新文学和民众民俗文化的联姻,使其在现实承载上抵近民众的精神内面,因由切实的国民性批判从而得以坐实其思想启蒙的旨意,竟而在强调和高扬反传统的主张之时,解除单向的西方参照所必然施之于作家主体的“影响的焦虑”,转而于本土文化内部或传统文化的边缘区域别寻变革的力量,为新文学的发展找到了些许源自于自身传统的能量和经验支撑。
(一)“平民文学”概念的形成
立足于精神启蒙和变革传统文化/文学的目的,“五四”新文学的民间化取向首先显现为新文学整体认知理念上的国民或“平民文学”概念的形成。
早在新文学发生伊始,1917年2月陈独秀即在其宣告新文学成立的纲领性文件《文学革命论》中明确界定,“文学革命”的努力目标首先就是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14]。他的“国民文学”概念,不尽等同于“平民文学”,但他在使用这一概念之时,有意识地将其和“贵族文学”加以对照,而且从修辞效果和言说态度两个层面揭示了“贵族文学”和“国民文学”的不同——不,应该说截然相反的——特征,其潜在的暗示自然使“国民文学”之“国民”概念内含了走向“平民”理解的可能。其后,应和并深化他的表述,对于平民文学概念,胡适和周作人等人遂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富有建设性的论述。其中,胡适主要从白话的提倡入手,主张废除文言,从通俗一路用力,将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对立,以为“中国文学史没有生气则已,稍有生气者皆自民间文学而来”[15]。而周作人则更为辩证和理性,立足于人道主义精神指引下的新文学“人的文学”特质的确立,在有关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的阐释之中,侧重于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文学精神的比较,以为平民精神是求生意志的体现,其所强调的是有限的平凡的存在,以入世为原则,而贵族精神则是求胜意志的体现,以出世为倾向,强调的是生存的无限的超越。缘此,理想的存在便是二者互补,使人的精神构成趋于健全。这种理解显现于新文学的建设,他得出的结论便是:“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16]
从学理分析,周作人的认知无疑显现了更为辩证和稳妥的成分,而胡适的看法则不免偏执和浮表,但是从新文学后来发展的事实看,因为认知内部深含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所以胡适的“浅”和“偏”显然较周作人的“深”和“全”更为时代所喜欢,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五四”影响下很长一段历史时段中,新文学价值取向中的民间成分无疑更为突出。“白话的”“通俗的”“为人生”之类的话语因此也便自然成了新文学建构的基本关键词提示,而周作人“平民精神”和“贵族精神(其实将精神换作趣味,也许更贴合周作人的本意)”结合的“平民文学”理念,在其实际的历史接受之中,事实上也便不自觉地偏向了“平民”这一身份标示而非他所期望的文学自身理想形态的建构。
别样的声音当然还有,如借镜西方天才理论而重申新文学应该是“贵族”或“少数人”事业的主张,如认同世界文学发展趋向而强调新文学不断的现代性的认知等,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对于传统社会权力阶层以及作为其附属的上层文学的不信任,所以“五四”知识分子所希冀建构的中国新文学,也便更多反传统、背身上流社会的民间属性。
这种民间意识的萌发,初始自然不乏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下个人立场的强调。传统文人信奉“学而优则仕”的自我价值实现模式,其意识深处寄植着“为相”或“为臣”的人生信条,痛心并警觉于这种自觉不自觉的人身“附属”意识,加之西方近现代以来“个人主义”理念的烛照,所以“五四”新文学的设计者们在其思维里,也便有了与那种“官文化”忤逆着的非官方的“个我”存在的强调。鲁迅曾说自己的思想原本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17]。他的情况不是个案,事实上,这种非官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主体意识强调,确乎曾是他们中很多人共同的精神诉求。从此出发,人们能够发现新文学历史建构中一种完全与传统主流文化异质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存在,——他们在精神上不愿附属于任何权力,自觉于官方的对立面,于传统和社会的双重批判之中确立自己自主的价值态度和文化立场。
不过,在意识到这种非官方或者另一种民间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存在的同时,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因为强大的“国民国家想象”意识的存在,所以“清末中国最大的课题是民族国家的形成”,缘此,“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不能脱离想象和建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18]。而正是受制于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需要,我们看到,这种对立于官方文化的个体独立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在现代中国并没有获得一种适宜的发展气候和土壤,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独自成为,相反,受制于外在社会语境的规约,个体混溶于周围人群,个体之人成为人国之民,其对立于官方的非官方属性也便和土地、和一般民众结合,转向或者趋向于社会底层,因之显现出了极为明晰的民间(国民的、俯身底层的)取向。
只有于这种倡言反传统的现代意识和精神诉求背景上用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立足于“国民文学”或“平民文学”的“五四”新文学区别于本质上为官方“帮忙”或者“帮闲”的传统文学的异质属性,——和服务于社会上层的贵族的、精致的古典文学不同,“五四”新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旨在启蒙或发动一般民众,希冀通过国民的积极参与从而坐实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通俗的、新的文学话语实践活动,并因此清晰,正是通过这种异质属性的建构,白话化、通俗性、民间性等“五四”新文学的内涵界定才有了真正的理论支撑。
(二)学术和文学的双面实践
观念引导行动,为身份属性上的“国民”或“平民”整体认知所指导,民间取向也便具化于“五四”新文学在学术书写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多种历史实践行为。
先说学术的。虽然从自然进化历史发展观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出现,不用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并且通过其“国民”或“平民”身份属性的认定,得以确立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中国文学在一时代的存在形态,这看起来极为自然的事情事实上还需要在学术上“验明正身”,举证充足的理由说明自己登堂入室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为了说明新文学的“平民”身份属性及其相关的民间取向的合理性,于学术一途,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努力。
其一,白话升格和方言调查。语言是文学的本体,立足于思想启蒙的现实写作动机,检讨此前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新文学的倡导者大都意识到了旧有的文言写作对于新思想传播的阻碍作用:一方面是太难,太过精致和含蓄,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接受的障碍;一方面是高度的书面化,长久的承袭导致了表达与生活的脱节,缘此,在充分意识到了问题存在的严重性之后,新文学的倡导者们遂以语言为突破口,反文言而倡白话,确立了白话文学在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主体位置。“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9]以此之故,他们不仅制作切音字母、简字谱录,积极推介普通话和白话文的应用,从文学的根本处建造新文学的审美机质。而且还着眼于文学和个性化语言的一体存在关系,积极对各地的方言进行调查和研究,补充和完善白话文的构成机制,不断升格白话文的审美表达水平。1922年北大国学门成立之后,门中诸人,不仅收编本自独立的歌谣研究会,而且还在歌谣是“方言的诗”或“方音的诗”的认知基础上,成立方言调查会,周作人、董作宾、黎锦熙、魏建功、林语堂、沈兼士等都积极撰文,从明晰的学术层面,为白话文学的进行和展开提供必要的支撑。
其二,口承文学的发掘。口承文学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是民族文学的最初形态,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极为普遍的民间形态。相较于文人的书面写作,它们虽然显得简单、粗糙,但是换一种眼光看,因为它们大都是民众的一些随心随性之作,保持着“劳者歌其苦,饥者歌其食”的基本特性,较少专业作家的功利心和程式化的匠气,所以它们不仅更能显现民众生活的真相,表露他们内在的心声,而且也在表达上显得更为朴素和简洁,更富有生机和活力。“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民间口承文学的重视和发掘,一方面是其民族意识觉醒,鲜明的思想启蒙动机使然;一方面则是西洋新的学术思想如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烛照的结果。早在民国初年,受英国人类学派理论方法的影响,周作人即在其家乡的报纸上刊发广告,公开搜集民间歌谣和童话,其后又连续著文,撰写了《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及《儿歌之研究》等论文,对于口承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的兄长鲁迅也和他一样,不仅在自己的文章(如《文化偏至论》等)里积极评价口承文学的意义、价值和现实功用,而且还积极配合周作人采录歌谣并征集童话,在教育部起草文件(参见《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号召建立国民文艺研究会,对于以口承文学为主的民众文艺进行专门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们兄弟的做法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1918年春天,为“文学革命”的呼声所激发,在刘半农、沈尹默的积极建议和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在1923年冬天编印出了《歌谣》周刊,一方面搜集选登各地歌谣,一方面对其进行整理研究,通过具体的学术研究为当时还处在摸索尝试时期的新文学特别是白话新诗写作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文本参照和努力方向,具体践行了《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所倡导的学术和文学双重目的结合的意愿,显见了新文学民间取向的切实成绩。受其影响,从口承文学抑或民间视野重新审视,原先隐身于各种文学史叙述中的民间歌谣甚或民间文学的成分也便不断为人所指认并推崇。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讲义(1921)不仅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归结为白话和文言两相较量离合的历史,而且更是在一些章节里极力凸显民间写作的重要性,如在汉魏六朝一章的讲解之中,他就只举当时的民歌乐府,而对于文人的写作则一概不论。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上,1923)也将文学分类为“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两种,并且毫不回避他对于平民文学的重视。在谈到汉魏平民文学的相关章节里,他明确宣称:“贵族文学,在文学史上,古人也有相当的(古典的)价值。现在作文学史的人是(以)词赋派文学为上,平民文学为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述乐府不过两页)。我现在反过来,以平民文学为重。”[20]且在具体的编置中,叙述平民文学的第二编,设六章,篇幅占了90余页(第37—125页),而对于同时代的贵族文学进行叙述的第四编,设三章,只占区区十多页(第149—166页)。他们的做法,胡适总结说:“最要紧是把这种升沉的大步骤一一点出来,叫大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比较的材料,也许可以打破我们一点守旧仇新的顽固见解。”[21]。很明显,一反传统套路,他们就是要在学术上为新文学的平民属性或民间取向寻求历史的支持。
其三,俗文学的被重视。“五四”新文学之所以目传统文学为“贵族的文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高度文人化的传统主流文学,太正,太雅,和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剧烈动荡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太隔,为此否决了传统文学发展的路径,从建设伊始,新文学便一路走向了通俗的方向。
这多少有点较劲的意味,传统太正太雅,他们就尽可能的俗白,矫枉过正,在许多新文学的开拓者心目中,似乎只有这样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行径,才足以证明他们反传统的决心和态度。时过境迁,人们自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偏执,但是这种偏执在当时却是一种必需和必要,其促使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使中国文学获得了一种异质的内容。而且,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爬梳相关的文献材料,我们亦能够明白,他们通俗化的努力,并非一味只是激情的表露,其中也沉淀了他们在学术上对于俗文学扎实认真的研究和思考。
他们对于小说的研究即为其中典型的代表。中国是一个诗文大国,所以谈及文学,传统理解也便更多以“抒情言志”的诗歌和“文以载道”的散文为主要的举证对象。清政府编四库全书用以显示其“文治武功”的盖世成绩,其全书号称包罗万象,囊括所有,但是一般的白话小说却并不在其关注之内,即如《水浒》和《红楼梦》之类优秀作品,也被冠以诲淫诲盗之名而排除在外。这种情况至“五四”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为精英知识分子立足于思想启蒙立场意欲和普通民众进行对话的强烈愿望所驱使,一方面是文学革命和语言改革所引发的白话文运动的发生,所以描述新文学在文体认知上的见解,一反惯常的“诗文正宗”观念,贬诗文而抬小说戏剧,胡适有言讲:“今人犹有鄙夷小说为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2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陈独秀也说:“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粲然可观者。”且以为中国文学发展至近代,前后七子及文派八家等使得“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23]。为了将小说抬进文学的正殿内堂,新文学的开创者们还倾其所学,对传统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进行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在诗学、词学和文章学之外,别建小说之学问,通过切实的努力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于此一面,胡适和鲁迅可作代表。其中胡适从1920年起到1925年末,接连进行了《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镜花缘》引论,同时还写作了《三国志演义》序、《三侠五义》序、《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官场现形记》序等,不仅给书划分段落、新式标点,而且还对作者身世、成书过程、书的内容、意义价值和技术优劣等给予必要的考证说明,推介并指导了这些书的社会接受,引发了人们对于这类小说的阅读兴趣。鲁迅对于小说史写作的兴趣萌发极早,1912年他就编成了《古小说钩成》并发表序言,此后又陆续编辑并刊行了《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等,其中《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撰写和不断的校订修改,显见突出的意义。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不仅改变了中国小说向来无史的尴尬,让小说这种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方式也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撰写过程中,他还不断破旧翻新,如谈小说而从神话、传说立论,予传奇、话本以专门的论述等,凸显他鲜明的民间意识。
除了小说,其他如戏剧、童话等俗文学,新文学先驱们一并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他们或极力宣传,积极倡导,或绍介国外理论,旧材料做新审视,在理性的思考梳理之中,从民间文化表现这一特殊的本土经验层面,寻求着可资新文学发展的营养和支撑。
再说文学实践。作为一种整体的价值取向,除却学术上所做的证明之外,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对于民间取向,“五四”新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首先是题材或曰内容选择上的。“五四”之前,已经有不少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众在政治革新运动中的重要性,为此,他们曾在诸多的言论中都谈到了关注和调动民众的必要性,不过,由于蒙昧于民众自身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即如鲁迅在小说《药》中所描写的革命者“夏瑜”一般,他们拼死斗争,将一切都献给了百姓的权力和利益谋求,因此他们响亮的革命宣言并不能为普通百姓所理解,他们的革命本身也演化成了一种悲剧,自己被杀头,自己所流的血也只能成为愚昧的底层民众制作人血馒头的无意义的材料。反省和总结此前改革特别是辛亥革命的教训,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由是特别强调新文学对于底层社会的关注。在《革命文学论》一文之中,着眼于国民文学建设的意愿,陈独秀明确提出了“平民文学”的理念,响应他的号召,周作人后来专门撰写了《平民的文学》一文,强调新的文学要突出表现“世间普通的男女的悲欢成败”,以达到“研究平民生活”,将“平民内生活提高”[24]的目的。胡适更是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力主新文学要特别注意关注“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种小摊小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25]。受先觉者理论的影响,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生活的书写表达一时间也便蔚然成风,不说文学研究会作家们着意显示人生“血与泪”的“社会问题小说”的出现,鲁迅执着于“下流社会不幸”和对于“貌似无事的悲剧”的揭示,20世纪初一批蛰居于北京的乡土作家对于他们偏远故乡一般人黏滞生活的表现等,单是“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人力车夫”一题的不同书写,其时一些白话诗人诗作标题的制作,如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劳动节歌》,如刘半农的《学徒苦》《卖萝卜》《铁匠》,康白情的《女工之歌》,等等,都可以清晰说明一个时代作家们在写作内容选择上的兴趣所在。
其次是文学语言和表达方式上的。从启蒙立场出发,在清晰了新文学在“表现什么”方面需得面向民间、关注普通民众疾苦的目标之后,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同时也意识到,新文学要吸引社会一般人,除了内容之外,在表现的形式方面也必须充分体现新文学民间化努力的方向,将新文学的艺术表达尽可能地和民众日常习惯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使新文学能够真正取代旧文学,为大众所喜欢并接受。其形式层面的民间化表现,具化于两个方面:其一,语言方式选择上的白话化努力。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它表情达意的工具,同时由于文学表达中情意和语言高度一体化存在的特征,所以也是它的本体。反思此前黄宗羲、梁启超等人所发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中国文学改良运动,有感于他们“旧瓶装新酒”的问题,所以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们一开始就从语言开刀,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目之为一种“白话文”运动,以白话的运行标示它鲜明的个体属性和自我身份。“逢新世界,新时代,新民族,当然同时要有新的舌头”[26],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感性的、浅表的、自然而然的简单演绎的话,那么更进一步,胡适其后的发言——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旧文字,死文字,既没有法子表现新思想、新感情,怎么能够创造新文学呢”[27],或“我们所提倡的革命文学,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28]之类,则显然有了更有建设价值的内容。言文一致,尽可能的通俗化、口语化,让汉字重新生动和活泼起来,让文学的表达真正能够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面颊。沿着这一取向,胡适创作了《尝试集》,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其他如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的写作,虽然面貌各有不同,但也都通过切实的努力,让中国文学从大雅的庙堂书案落实在了通俗的民间,成为了新思想和新的审美情感的有力传播渠道。其二,诗歌体裁参照上的民谣化实践。诗是文学中的文学,作为文学性体现最为充分、审美要求最为严格的文学体裁,新文学能否和旧文学叫板进而取代它,极为重要的考量指标即在于新诗的表现能否取悦于一般受众。否定了既有的精致但又因为高度成熟而渐趋僵硬的古典诗歌表达,虽然有翻译的外来诗歌异样启示,但是一方面是翻译本身的数量的限制,翻译质量的不敢恭维,一方面是作为异质表达的翻译诗歌的水土难服,所以在不断寻求来自于异域经验参照的同时,新文学的开拓者亦不断在既有的本土传统中寻求着经验的支撑。他们所发现的就是民间歌谣。这种发现,源自于两种基本的考虑:第一,民间歌谣是一种异质、别样的中国诗歌经验的构成,它区别于体现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意识诉求的主流、经典诗歌,显示出了更多非主流的民间、边缘属性,当新文学对于传统诗歌予以了“弑父”行为的反叛、否定之后,这种非正统的传统或者说中国诗歌内部的边缘性存在,其异端和本土的双重存在特征,因为吻合了新文学反传统同时又仍然隶属于中国诗歌的身份特性,所以也便自然引发了正在四处问道的新文学先驱者们的关注兴趣;第二,作为一种诗和歌高度一体化的民间传唱艺术形式,区别于文人诗歌高度书面化和精英化的存在特征,民间歌谣的口语化、通俗性审美特性,因其和“五四”知识分子立足于思想的启蒙而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向其学习,让诗歌成为表现普通民众情感和精神诉求的便利艺术方式,自然也就成了许多白话诗歌倡导和实践者们的自然选择。“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情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视野,就从此开场了。”[29]歌谣和文艺,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开始就存在的这种兴趣,其后进一步发展,明确成为胡适所言的“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因此“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的发展”[30]的思考认知之后,新文学的许多发起者——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便不仅积极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而且也有意识地向民间歌谣学习和借鉴,创作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的歌谣意味的新体诗歌,为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建立了最初的范本和努力的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向下看”意味以及在此大背景下新文学鲜明的民间取向,从内在营造了民俗学和文学结合的良好机遇和氛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历史语境的还原,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并不为一般学人所关注的民俗学,和许多先进的思想和学问一样,在强烈的民族精神复兴和问道于西方的现实动机的推动下,原本是被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目之为“显学”而加以引进的。为这种认知所导引,“五四”时期,很多的文化人都曾关注过民俗学问题,而且绝大部分关注的人都是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的人。
身处这样的时代环境,加之鲁迅本来就是民俗文化研究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早期进行民俗文化搜集和研究的人,又大多是他的同事、朋友或学生,他与他们在当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基本一致的文化取向和话题视野,相互之间的熏染和促进,鲁迅写作——不管是文学性的创作,还是《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纲要》等学术著作的写作——民俗文化兴趣的发生,也便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1] 刘玉凯:《鲁迅的民俗学观》,见《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2] 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民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3] 梁启超:《发刊词》,见《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2月8日。
[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5]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连载于《晨报》1919年2月。
[6]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7] 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0页。
[8] 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9页。
[9] 鲁迅:《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10] 钟敬文:《关于民间文化》,见《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页。
[11] 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见《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6—87页。
[12] 周作人:《〈歌谣〉周刊发刊词》,见《歌谣》第1卷1号,1922年12月17日。
[13] 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14]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见《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8日。
[15] 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见《大公报》1932年1月5日。
[16]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见《晨报副镌》1923年8月1日。
[17] 鲁迅:《两地书·二四》,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18]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2页。
[19]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2卷第5期,见《新青年》1917年1月1日。
[20] 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第2编第1章,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21] 胡适:《序》,见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8页。
[22]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第2卷第5期,见《新青年》1917年1月1日。
[23]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见《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8日。
[24] 周作人:《平民的文学》,见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25] 胡适:《新文学运动》,《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页。
[26] 志希:《书报评论·少年中国月刊》,见《新潮》1919年第2卷第1号。
[27] 胡适:《新文学运动》,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2页。
[2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29] 刘半农:《国外民歌译》(第1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第1页。
[30] 胡适:《自序》,见《词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