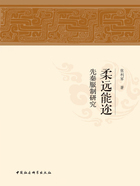
三 服制与国家的形态
学界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有多种理论,如侯外庐较早地提出“城市国家论”,将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追溯至晚商时期。[16]但该说并未在中国学术界延续,中国学术界主流在较长一段时间仍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准的奴隶制、封建制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的性质与形态问题。日本学术界主要以“都市国家”和“邑制国家”解释中国商周至春秋时期的国家结构形态。[17]冈村秀典在分析以上早期国家特性说基础上,从王权与祭祀两大角度考察,提出早期国家为祭仪国家的特性。[18]
苏秉琦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三模式为“古国—方国—帝国”[19],得到多数考古学者的支持。王震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卓识,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表述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或可称为初始国家)是小国寡民式的邦国,邦国的进一步发展是王国,王国以后,通过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走向了帝国。[20]新近公布的清华简《厚父》可能是商周典册档案的战国楚地传抄本,透漏夏代可能已建立服制。[21]简文还提供了中国国家起源的一种理论解释,《厚父》第5简载夏代遗民贵族厚父之言“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22]。厚父将建立国家归于上天,并且谓天降民而设立万邦,并为万邦设立君主、长官,目的是希望君主、长官协助上帝治理下民。这揭示中国早期国家最初的形态是万邦并存,与《左传》《史记·五帝本纪》等传世文献记述黄帝、尧、舜、禹时代为万邦、万国时代相应,亦与新石器时代后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较为广泛出现的石头城邑相适应,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邦国。古文献记载,黄帝族邦兴起前的神农氏时代应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农耕文明已有较快的发展,被古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古史上的盛世时代,但农耕文明发展到后来,不同的氏族、宗族、聚落之间发生了争夺、冲突甚至战争,然后才有黄帝族做兵,以武力制止史前的战争,可以说黄帝族是以军事实力胜出的族邦,黄帝族邦征服和联合一些大的族邦,形成以黄帝族系为核心的族邦联盟形态的国家。这个国家仍以强大的武力为统治基础,黄帝族武装巡狩这个国家内的众多族邦,随时征讨叛逆者,至尧舜时代可能都是族邦联盟国家形态,尧舜时代的巡狩应是此种治国策略的延续。在舜之时,这个族邦联盟国家首领的权力逐渐加强,吸收周边各大族氏的首领进入国家担任各级职事。因舜时代的治理大洪水,使得国家对联盟的各族邦的控制加强。因禹受舜命治理洪水成功,禹及其族邦在族邦联盟国家中的影响力加强,禹受命建立了夏邦。
禹通过征讨三苗、涂山会盟诸侯、制定贡赋制度、铸九鼎逐步确立了对于天下万邦的王权统治,禹成为夏王朝的奠基者,为邦国联盟国家向王朝国家过渡铺平了道路。夏王朝发生的观扈之乱、太康失国等可认为是王朝国家形态尚未稳固。然自少康中兴之后,王朝国家逐步发展,至于商周王朝时期王权逐渐强化,王朝国家的结构形态渐趋完善。夏商可能进入到氏族封建为主体建构的王朝国家,至于西周时期,周成王、周公借东征平叛之机,平定天下四方,通过推行宗法封建制重新构建西周国家结构形态,西周则演变为宗法封建为主体的王朝国家。[23]进入东周承续西周宗法封建制而又有新的变化,周王居于洛邑,直接控驭地区逐渐缩小,处于诸侯包围之中,王朝事务多依赖于诸侯国的支持,勉强维持周王权威。由春秋至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结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发生重大变革,至秦统一,中国古代国家进入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时代。